芦苇啊,芦苇
难道还有旱芦苇?家乡一百多户人家,河流几十条,宅前宅后都是水,总不见得长到竹园里去,那不是芦苇的地盘。但有时也要相信一下的,到河边上
母亲告诉我,海边村的芦苇都叫水芦苇。
难道还有旱芦苇?家乡一百多户人家,河流几十条,宅前宅后都是水,总不见得长到竹园里去,那不是芦苇的地盘。但有时也要相信一下的,到河边上走一圈,会看见一部分芦苇确实长在岸上的,这个岸,海边村的人叫浜滩。
浜滩的芦苇长相有点苦恼:一是明显的矮,跟甘蔗、芦粟一般长;二是粗,跟收梢的小芦粟差不多粗细。
芦苇是聪明的,到了海边村,想活个命,活个好命,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己,这个道理书上说是物竞天择,我们叫识货,意思是懂得自己、懂得别人。水芦苇明白这个道理,它用它的艰难抉择与生命事实证明活着比委屈更重要。
家乡的水芦苇就像打仗的战士一样,趴伏在几十条河流边上。
但我一直感觉,漫天漫地的芦苇,是上天对家乡不经意的恩赐。
立春的季节,是看不到芦苇的,芦苇还在睡觉。春分来了,到河边去看,偶尔会看到河水里竖着的茎草在随波荡漾,那是小芦苇。夏天来了,芦苇就从水里冒了出来,那速度与我们凫水后突冒河面的架势一样,都是刹那间的事情,但芦苇没有声音,我们的声音稀里哗啦。
在水里的芦苇最容易长大,先前是鹅黄般的小头,尖尖的,匀布于河面两边,像在守护着河流。一夜过去,一周过去,一月过去,芦苇就会高过我们的人头。家乡的芦苇,家乡的速度。每年这个时候,所有的芦苇总是以全新的姿态莅临村庄,而且一定以最朴素、最古老、最文静的姿态,将海边村打扮成绿色里的小村庄。
其时,我们开始盼端午节。挽一弯芦叶闻粽香。海边村人历来叫“挽”芦苇的。我们握着长柄弯钩,伸出右手将河边上的芦苇钩到眼门前,再伸出左手抓住芦苇,然后用右手将芦叶往下掰下来,最后将芦叶放到花袋里。挽好后,及时放钩,一放钩,芦苇又全部弹回到原处,站着不动了。
宅前宅后河里的芦苇挽光了,就约别人家孩子一起去别处挽,挽了一些辰光后,我们就在浜滩边上玩纸牌,玩捉迷藏,至于芦叶挽了多少、够不够,都不管。分手时,大家从花袋里倒出芦叶,你一把,我一把,匀好后就回家。
芦苇很快长出了芦花。青蓝色的芦花会马上变成白乎乎的芦花。芦花一白,芦苇叶白了,从芦梢到芦身,像是无数的幕布拉在河岸上,水面绿茵茵,水上白茫茫,那样子,真叫一个少见,也真叫一个好看。
芦花也是不能浪费的。父亲说,我们挽芦花去。也是用原来的长柄弯钩,把芦苇钩进来,但芦叶是掰断的,芦花是连芯拔的。芦芯在芦叶的包裹之下,是不愿意走离芦苇的。走离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芦花不懂,但不离不弃是它的做派。
大冷天,农事不紧,父亲开始做扫帚了,原材料就是芦花。将五六根芦花并在一起,扎成姑娘的辫子模样,再挨序排列,成了蒲扇样子,然后用剪刀修一下,安上一个竹柄,就成了一把芦花扫帚。这扫帚扫地,特别着地、滑爽。芦花扫帚扫过的地皮,颗粒状的尘灰是没有的。
芦苇最受欢迎的是芦秸秆。芦苇收割回来,放到仓库场晒干,再捆成一捆捆,然后由村里分配到每户人家。芦干是用作盖房的。是将芦秸秆编织成芦席或者芦笆。房子上好正梁,钉了椽子,椽子上面就放芦苇,然后再盖稻柴,稻柴要盖半尺厚,盖好后用稻柴绳织成的帘框盖住,大风就吹不掉房顶,家就多了一份踏实与安稳。
芦苇啊,不需要我们服侍,也能够茁壮成长。长大后,芦叶可以包粽子,芦花可以做扫帚,芦干可以盖房子,可以做芦笆。我对芦苇服帖到底,觉得它的奉献惊人,而真正让我对芦苇产生好感的是芦苇的根,我们那里叫它为芦根。
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们就到河里,荡开芦苇,寻找哪处芦苇长得最密、最粗、最壮,干什么?我们要顺着芦苇潜水下去,去挖一根芦根吃。
芦根长在泥土板结、河水清冽的地方。第一个凫水动作,只能判断芦根的生长的位置;第二个凫水,只能摸到芦苇的根;第三个凫水,挖掉芦根周围的河泥。要来回好几次,才能摸起最粗的芦根。我们人小,气短,只好轮流凫水,谁拔出来不管的,反正都是大家的。
芦根拔到了,首先是分给把芦根挖出水面的人,是以结果论英雄的,大家都没有意见。然后根据芦根的长短,每人分到一节或者两节,就齐伏在河边吃芦根。芦根的吃法与芦粟的吃法一样,就是大口大口地嚼,把芦根的水嚼出来咽到喉咙里去。芦根的水甜津津的,一点也不腻,吃了不会泻肚。
几十年过去了,老家的芦苇几乎没有了,芦根自然也挖不到了。那长得白白胖胖的根,那甜甜蜜蜜的根,不知道去了哪里——想来是这样的:我已走出村庄,芦苇也走出村庄,我对芦根的眷恋已经在我住的城市里发生。既然这样,把芦苇藏在心底,应该是最合时宜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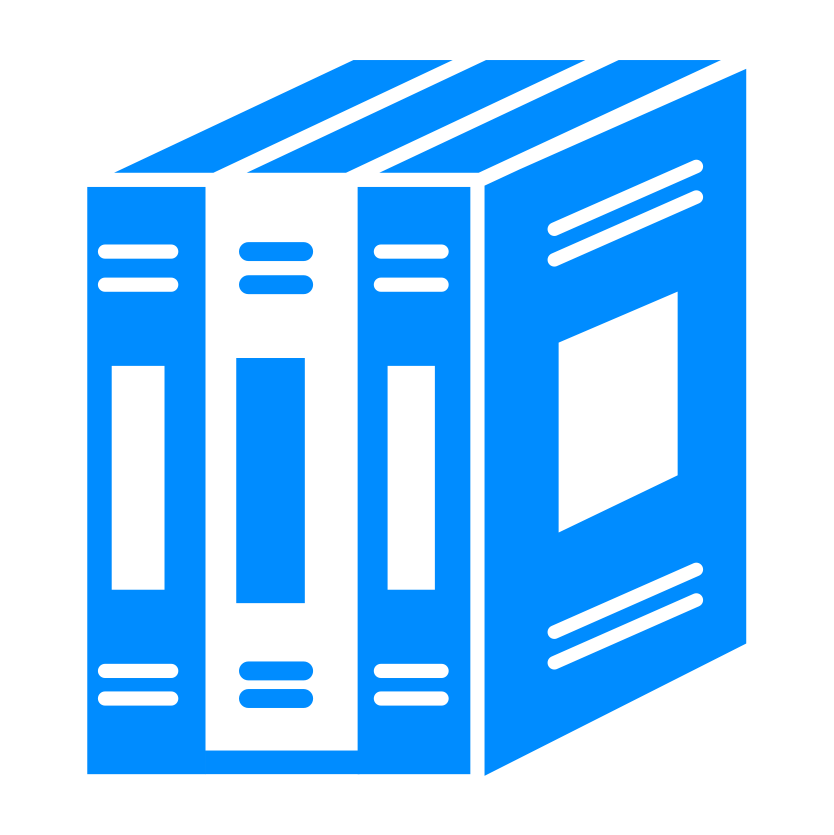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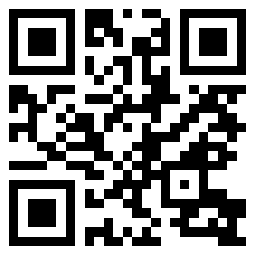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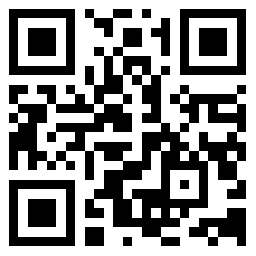
 微信收款码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