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给予少年心灵的滋养
那天下午课间,班主任把我叫到一边,让我放学后去她办公室。我不知道她为何找我去那里,两只手掌立刻由热转凉。一般来说,被老师叫去办公室总是因为做错了事。
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在上海新闸路一小读三年级。我磨磨蹭蹭来到教师办公室,站在门口,眼睛只敢看脚下,心里怕得在打鼓。忽然,听见班主任在轻声叫我,我抬起眼来,看见办公室里面一群老师都在忙碌,班主任在对我招手。
我身体僵硬,挪到班主任的写字台旁边,眼睛看着台面。
班主任拉开写字台右边最上面的小抽屉,拿出一张硬卡片,比香烟盒小一圈,很薄,淡蓝色,告诉我,这是上海少儿图书馆的借书证,给你。
原来是这事。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松弛了。我的小学没有图书馆,但我知道图书馆里都是书,老师们上课时都说过。
我笑着点点头,心想看书我是喜欢的。
班主任说只有一张,说着看了我一眼。
我那时只是十岁,但是完全理解了班主任这句话里和看我的眼神中所包含的意思,那就是让我不要把这事告诉其他同学。
我又点点头。
班主任给了我一支钢笔,让我在借书证的第一页上写上学校和自己的名字,还告诉我少儿馆在南京西路石门二路附近,新华书店的旁边。
我谢了班主任,把我人生的第一张借书证放进衣袋,乐呵呵地走了,心想这下有书看了。
出了校门,我很纳闷,班主任为什么把极为稀缺的借书证给了我呢?全校同年级有六个班,全班有四十八位同学。但我清楚,她知道我喜欢看书,她知道我的语文成绩不错,她知道我文质彬彬。确实,我一直喜欢阅读,似乎天生,也绝对主动自觉。
我新闸路永吉里的同号邻居中有在读高中初中的,文革开始后,不读书成了风气,她们的各种书籍也就成了累赘,被她们的大人一股脑儿丢在晒台上,一大堆,小山似的,其中有她们以前的课本,也有她们以前购买的文学作品和订阅的少年文艺杂志。
我发现书山后,很高兴,像遇见了宝藏一般,挑了一本,好像是初中的语文课本,就看了起来,也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就是喜欢看,认识的字就看下去,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或者根据认识的前后字猜测那个不识之字的大概意思。起先我站在那里看,后来累了,就蹲着看,不管日晒风吹,再后来,征得她们同意,借回家读。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一个多礼拜。
某天,我又去晒台换书,那里竟然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问,才知道那堆书全被卖掉了。我顿时萎靡起来,好几天都没有精神,似乎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突然不打招呼就离我而去了。
没有了书看,我就去街上的阅报栏看报,不是专门去看,但只要路过,就肯定会停下来去阅读。有一天时近黄昏,我妈让我去新闸路大通路口的杂货店买牙膏。那时买牙膏,可以凭用光了的牙膏皮抵扣两分钱,还可以让营业员去掉新牙膏外面的纸壳包装再抵扣一分钱。我付了去掉三分钱的购货款,握着圆滑溜光的牙膏,想着马路对面有个阅报栏,便穿过马路去向那里。
日光不济,阅报栏前读报的人不少。我那时已经近视,又不肯戴眼镜,在后面看不清楚报纸的细小铅字,就挤啊挤的,到了第一排,把牙膏握在胸前,仰起脸看了起来,一直看到天色几乎全暗,辨不清报纸上的字才回家。我并不知道,那天班主任正好在新闸路上行走,路过阅报栏,无意中发现了我前挤的身影和贴近阅报栏玻璃的脸。第二天上课时,她在班上表扬了我的喜好阅读。
但是,可供阅读的文字还是太少,特别是文革初期,造反队视家庭藏书为敌人,欲搜光烧尽而后快,有书人认家里有书为不忠,就撕碎卖光以避嫌。有时,我只得看马路上贴着的大字报,短的一张,长的十几张,甚至几十张,一溜贴开去,刚贴上的还在沿墙往下趟浆糊,像一挂长鼻涕。有时,我接过马路上散发的花花绿绿的油印传单,站着捧读。读这些东西让我难受,有点像没有吃饱,老是肚饿的感觉。
因此,这张少儿馆借书证的突然光临,意义之重大不下于饥荒年代给我增加了粮食定量,给我添加了肉蛋鱼虾,会使我有饱腹感,会让我脸上无菜色。
有了借书证,我带着它就去了南京西路上的少儿馆。我从没进过图书馆,一路上思绪飞扬,图书馆里的那么多书是怎么放置的?像我家晒台上那种堆法,显然不行,埋在最里面的书怎么取出来呢?大概是一本一本叠堆在桌上,顶到天花板,这样也有问题,最上面的书该怎么拿下来呢?踩在凳子上?爬到梯子上?
胡思乱想中,我就到了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
南京西路是上海最热闹的商业街,各式商店一家挨着一家,连绵十里不绝,店内人头攒动,店外摩肩接踵,电车汽车轰鸣着来来往往,自行车三轮车叮叮当当地飞来驶去,时不时,一辆卡车慢慢开过,车厢围栏上贴着打倒砸烂的白纸黑字标语,车厢中立着义愤填膺的红卫兵们,一手举拳高喊口号,一手揪住几个挂着打X牌子的人的头发。
然而,一拐进这个不宽的弄堂,一看见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白底黑字的竖挂木牌,一走进这扇漆黑格珊铁门,我立刻觉得沉静安宁主宰了这片小世界,仿佛这里是个无人之处,但整洁干净的水泥地、青绿欢腾的爬山虎、明亮无尘的窗玻璃分明在告诉,这里处处透出人的灵性,这里处处显出人的儒雅。门卫简单问询后,指引我去一栋小楼的二楼。
楼里一如楼外那般宁静。楼梯是木制的,不新,旧得端庄深沉。红褐色的扶手光亮且宽厚,以我那时的手掌,尚握不住。红褐色的踏步不是直上的,有个小弯,方能抵达二楼。二楼有个房间,门口似乎挂着少儿部的牌子。我估摸自己属于这一群体,就轻手轻脚走了进去。
一进门是条宽度可容两三个小孩的长夹弄,一边是墙壁,另一边是一个一个并列的柜子,几分钟后我知道了,这柜子叫书架。我打量着书架。每个书架从下到上有五六层,每层都立满了书,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看上去整齐舒服。我想,要是能和这么多书住在一起,不停地看,该是多么开心。书架的每层都有上下两块间隔两三指宽的玻璃挡板,透过玻璃和空档,可以清楚地看见书脊上的书名。我又想,原来书是立在书架中的,这样找起来拿起来多方便啊。并列的一排书架当中少了一个书架,形成一个缺口,平放着一块齐胸高的木板,像商店里的柜台,可供办理借书还书业务。从柜台看进去,两个工作人员在里面伏案工作。
我轻声询问。一个男性工作人员和蔼回答,你自己看书架上的书,看中哪一本,手指伸进玻璃空档一推,我就知道了。
我就是这时候知道书架这个单词的。
我弯下腰,双手撑住膝盖,看书架下面两层的书。我直起腰,看书架中间两层的书,又退后一步,仰脸看最上面一层的书。我一本一本看过去,几乎看遍了这么多书架上的每一本书,当然,看见的只是书脊上的书名。我凭仅有的知识,从书名猜测书的内容,最后,选定了一本,把食指伸进空档,伸向那本书,推了一下。它的一部分倾斜了出去,使它突出于它的朋友们,就像队列里调皮的同学伸出的一个嬉笑脑袋。
那位工作人员走了过来,拉出这本书,要了我的借书证,在证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把书和证一起给了我。
我打开借书证,看见上面写着书名、借出日期和归还日期。我把借书证夹在书里,把书脊朝下,平整地放进书包,注意不让它上面的两只书角抵到书包而翻卷。
我脚步轻盈,几乎弹跳着走出少儿馆,来到南京路。那里照理应该熙熙攘攘,但此时在我眼里只是空无一人,盖因我的脑子里只有这本刚从少儿馆借来的书,其他的都与我无关。我很想找个墙角站立,拿出书来马上一解饥渴,但我忍住了,这个年月,街上抢东西的事时有发生,比如抢军帽,抢像章,如果书被抢去了,我怎么办?我看不到书当然事大,但怎么向少儿馆说清楚更是难题。
第一次借的是什么书已经没有印象,一共在少儿馆借过几回书也毫无记忆,但是从那些书中摘抄的好词好句记得倒是积了一厚本。
有一件趣事至今不忘。一九七一年年初,刚进中学后的某天,我去少儿馆还书,心里很惆怅,一路走得慢慢吞吞,就是不愿意很快走进那栋小楼。少儿馆的借书对象是小学生,作为中学生,我显然不能再在这里借书了。我心有不甘,还书的同时试着又借了一次,竟然成功了。借书竟然可以继续下去!我捧着书,高兴得一路哼着小曲回家。可惜好景不长。下一次还书时,工作人员毫不留情地收走了我的借书证。
从此,我再也无缘走进少儿馆,走进这座陪伴了我三年多的书的殿堂。长大后,每当路过这个地方,我总要望住这栋小楼看上一会儿,任凭往事在心里翻滚。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少儿馆的图书供我阅读,我会怎样打发少年时代那些不需要认真上课的百无聊赖的日子,抑或就成了与读书背道而驰的心灵干枯的人也不是没有可能,果真如此,就没有如今拥有硕士学位和高级职称、担任企业高管的我了。
不过,我到现在都没明白,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打倒走资派,砸烂封资修的年代,为什么少儿馆的借书业务竟然依旧开展,而且能够持续下去?
要说少儿馆的哪本书对我的成长最有帮助,我还真说不上来。不过,这没关系。我们从小到大,吃了无数顿饭,说得清楚究竟是哪一顿饭增加了我们的脑力,促高了我们的身材,强壮了我们的力量?说不清楚,但哪一顿饭都不可忽视,也不可缺少。读书也一样。读过的无数本书中的每一滴营养,都默默流淌于我们的血肉,都悄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最终形成对社会有益、对个人有用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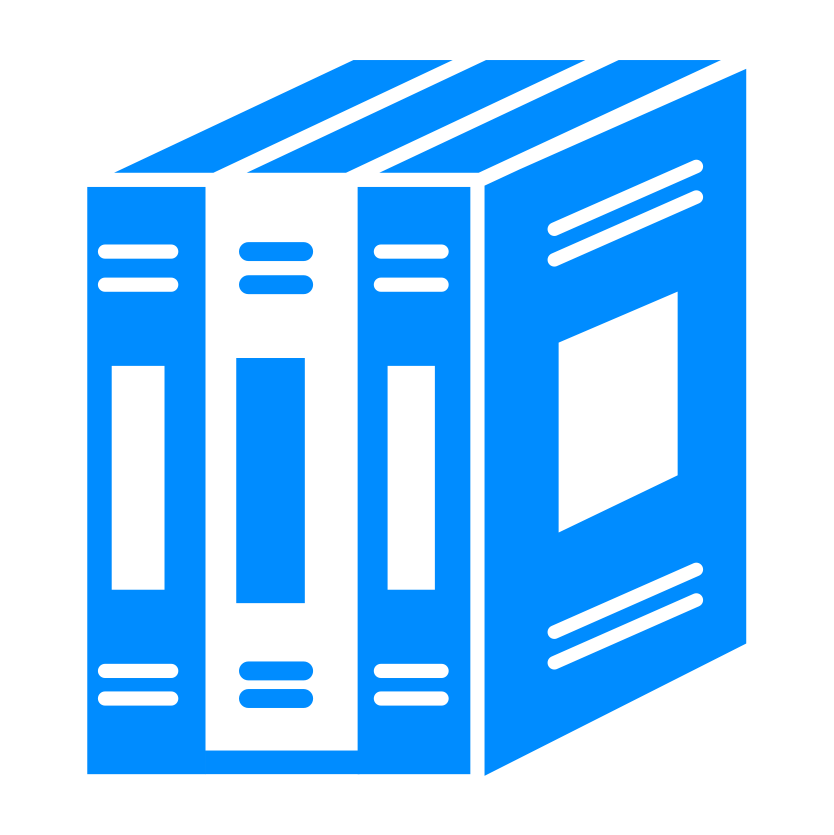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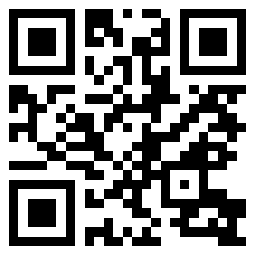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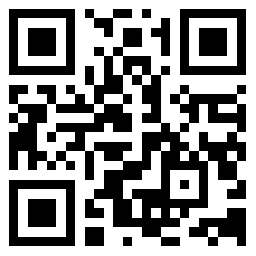
 微信收款码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