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拥有诗意的世界吗?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喜欢动笔写一些东西。有时候随口吟诵出一句话,想留下痕迹落于纸上。可写完了这一段之后,却又发现没有了下一段可以续。记得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天真烂漫却胡诌一些离愁别绪。什么踮起脚望着你远去的帆,我的心和海上的雨一样纷乱(那时都没见过海,18岁才第一次看到海)。诸如从不怕夜的黑,只怕你皱着眉,夜的黑有灯火点亮,皱的眉是你的伤悲……真应了辛弃疾的名句,为赋新词强说愁。
如今生活的地方转了四五处、工作也换了三四个,也算是经历了一些人生不同的滋味,却发觉文学的细胞越发枯竭了。不愿像学生时代卖弄浮华辞藻,堆砌成一段段对称美丽的文字。也难以像前几年沉浸爱情中,日复一日的不知是唱出还是写出妄言呓语。慢慢的居然有了麻木颓废的感觉,很少再有年少时候那些极易引发的感触。开始迷恋一些慵懒但易成瘾的东西,捧着手机靠在沙发摆弄着各种应用程序。开始变得越发现实主义,没有好处对自己无益的,皆不愿去触及。开始变得拈轻怕重,困难的漫长的事情都不愿意坚持,只想求些立竿见影的成效。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孩提时代我们拥有的,应该是浑然天成的诗意,那时候的诗意亦可以称作童话。少年时代我们拥有的,应该是亲和游戏的诗意,那时候的诗意大抵来自于天真无邪。青年时代我们拥有的,应该是青涩爱恋的诗意,那时候的诗意是朦胧美好的回忆。可成年的我们呢?早已不再天真,也不再相信童话,很少有亲和信赖的朋友,爱情越发变得急功近利,甚至得不到至亲之人的理解……在纷乱忙碌且让人心累的现实世界中,我们丢失的诗意,又能从何处寻回呢?
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至少在工作的八小时之内是这样的,中庸之道也可能是千百年来恪守的准则,低调内敛可能植根于于国人骨子里。这两年我读书很少,完整看完的更是少之又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便是其中之一。也许我们从平庸到不平庸,中间隔了个“孙少安”,而从平凡到不平凡,中间又隔了个“孙少平”。在我看来,大部分人都能做到不平庸,简单来说就是都能让自己过得更好。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取得更好的成绩,在单位里谋求向上争取更高的职位,在商业市井里摸爬滚打赚更多的钱财……不平庸带有一种“比”的心理,意思是我不能比别人差。
但一个人想要做到不平凡,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在弗洛伊德心理动力论中,本我、自我与超我是人内心世界的三大部分。不平庸即超越了本能的我,基本实现了自我。简单来说就是我过自己本该拥有的生活,并能在这样的生活中获得实际的回报,但更多的是活在别人眼里,去实现别人认为你应该取得的所有。而不平凡则是在实现自我的基础上,进一步飞跃达到了超我的层次。这就呼应了前面讲的诗意的世界,一个拥有绝对诗意世界的人必然是超脱了自我的人。
古今中外,诗意的世界存在于各种经典。上一段讲的弗洛伊德的超我,带有诗意的成分,因为真正超我的人少之又少,超我甚至有了超人的意味。歌德从《少年维特之烦恼》到《浮士德》,始终拥有诗意的世界,从情窦初开少男少女的情怀,一直到浪漫主义的时代史诗。纪伯伦说,一个人有两个我,一个在黑暗中醒着,一个在光明中睡着。也许每个人都有两个我,希望你八小时内踏实工作,八小时外享受惬意的生活。
庄子从《逍遥游》的绝对自由主义到《天道》的安时处变、顺应自然,从“老子天下第一”的自由自大到顺应天道、遵循法则的超然脱俗,是一种升华了的诗意。庄子本身就是一首诗,包括他本人以及所说所作。“庄生晓梦迷蝴蝶”就是例证,这里又有了“诗化哲学”的思想,让指导人生的总学问也带有了诗意。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也许我们不能像诗人李白那样,时时刻刻拥有着激情迸发的感觉,但请你在欢聚畅饮时,面对亲人、爱人和朋友时,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2019年1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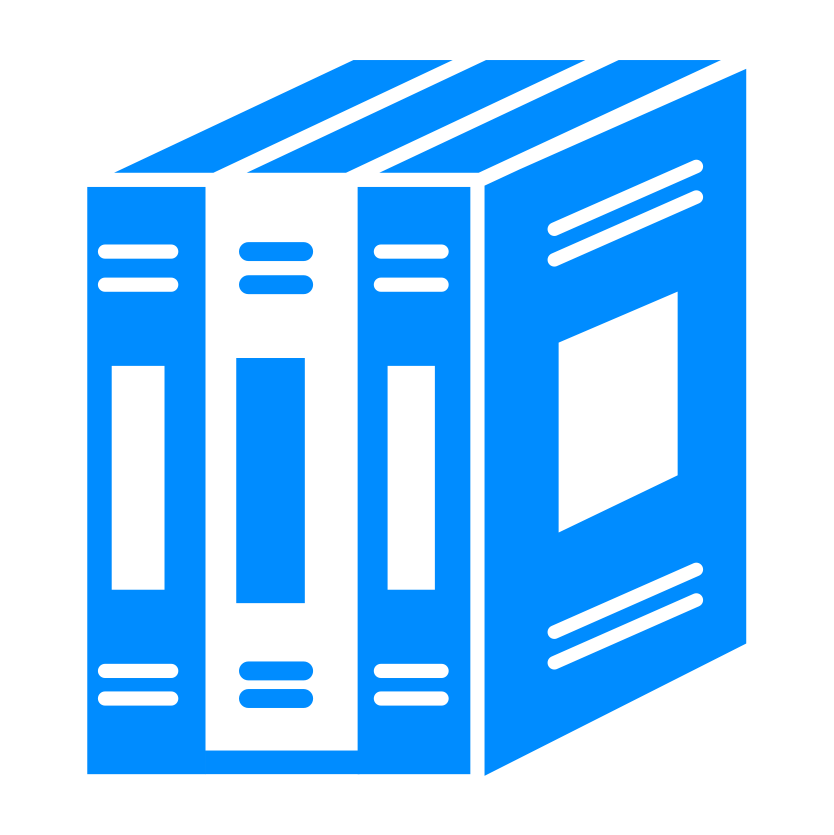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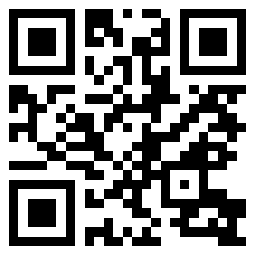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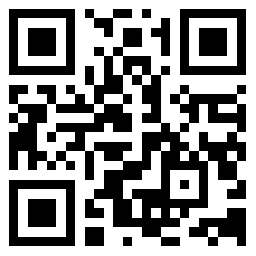
 微信收款码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