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烟火
家乡还能寻到一些传承下来的老习俗旧技艺,这些手艺一直坚挺的绵延着故乡的烟火,聊以代表着家乡,栓住那些天涯游子的心,能让我们身着洋装时,偶尔还可回味起家乡的味道,想象出原来穿补丁、着布鞋的土气模样。这些古老的行当虽然现在已由繁化简,淡去了原味,但勉强保留下来的形式,多少还能秉持着一些农村人的特性,以至于我们还能寻着它的根源,追溯着找到家乡!
在这些慢慢没落的传统习俗中,能让我们念念不忘的事务,大多都与年味有关,与美食相联。可能是先祖们在饥饿游戏里沉浮太久,他们对食物的膜拜和渴望,远远胜过其他任何俗事。在少有的富盈年月,丰收后的喜悦会开启先祖们的聪慧,那种聪慧大多体现为怎样化腐朽为神奇,去开发简单食物的更多口味品种,满足味蕾上不断变换的渴望和腹中需求,在林林总总的传统手艺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可能要算是打糍粑了!
糍粑是农村人难以割舍的美食。他无需繁杂的佐料,繁琐的操作,简单质朴地散发出诱人的清香。糍粑即能在饭锅上蒸,又可以水炉里煮,方便在锅中煎炸,任何一种烹调方式,都可不改原味又各有千秋。最有趣的是孩童年纪的糍粑,冬日暖阳下赶野火时,在火堆旁烤上几块从家里偷带出来的糍粑,守候半响,一缕焦脆声,唤起多少馋欲,罔顾小伙伴的嘲讽垂涎,也不理会烤焦或是夹生,猴急狼狈的往嘴里送,烫得嘴上起小泡,疼着直咧牙!
糍粑在农人心中的江湖地位之所以崇高,最主要还是它耐久抗饿。吃上三两块糍粑,可抵得上两大碗米饭,闲时可节约粮食,一天只吃两顿,忙时节省做饭的时间,又很好的提供体力。糍粑松软可口,老少皆宜,还可作馈赠亲友的礼物。是农村里能拿的出手、称得上心,得到城里人认可,又能储存得久好东西。
打糍粑在农人心里是件大事,有着过节般的仪式感。大约是冬至前后,农村里一般是完成了一年活计,左邻右舍便会合计出结果,趁哪一日天气暖和,大伙一起将糍粑打了!于是,存蓄好的人家,会抬出陈年石头碓窝子,里外仔细清洗干净,挖个小坑浅栽于晒场宽阔处,削整好专门杵糍粑的杵棍,等待打糍粑的日子来临。
打糍粑的前一日,各家将精心筛选出来的好糯米淘洗好,用冷水发泡一夜。第二天清早,勤劳的主妇心怀虔诚,上香敬谢灶王爷这一年的保佑,许下来年的愿望后,将泡好的糯米沥干水份,上入木甑再土灶大锅干柴烈火蒸熟。
当蒸好的糯米饭趁热倒进碓窝里时,屋场上应该已是非一般的热闹了。老少妇孺围着圈讲着笑话,年壮男丁手持杵棍,踏着碎步火热地朝碓窝里杵将开来。杵棍间进退有序,如鱼儿跃水,似乳猪寻食,碓窝里棍杵棍,棍赶棍,杵手喘着粗气围碓窝子转圈,还不忘谈笑着远近趣闻,花边乐事。期间穿杂着看热闹孩童天真疑惑的追问,好事者的歪理侃谈,年长老人斯文调武的娓娓道来。
糯米饭一遍杵好,其他杵手便可短暂停歇,只留两位精壮而有经验的杵手相对而立,手中杵棍互搅缠绕,猛一使劲,杵棍便将整坨糯米饭擎向天空,再漂亮地翻个边,咦~哟~呵~,围观旁人的壮气吆喝中,糯米饭被势大力沉地摔在碓窝心里。随着碓窝里的一声清脆,伴随着周围的齐声喝彩,众杵手又再次围将开杵。
一锅糍粑杵好后的间歇,嘴馋的小孩会趁机曲缩着通红的小手,夺上一根杵棍抱在怀中,费劲地啃咬杵棍上粘连的糍粑馅子。孩童嘴唇上的淌出的鼻涕,粘连在入口的糍粑馅子上,有一丝丝甜,也有一丝丝咸,那馋嘴滑稽的模样,赢得旁人又是一阵开环大笑!
农村人打糍粑一般都是五六家,最多十几家一起打,打好的糍粑明晃晃地摆在那里,似乎预兆着农村人清幽淡雅,甘甜绵长的生活。浅浅的一眼碓窝,盛载着清心寡欲的老农民,对自给自足的浓浓满足。
诗人说有炊烟的天空,才有歌谣般的田园生活,才有农家风味的可口饭菜香。在农村的土灶前,总会有一位慈祥健硕的老奶奶熟练操作锅碗瓢盆的身影。老奶奶土灶前的袅袅炊烟, 曾经是那样执拗地炙烤着我们心急火燎的食欲。
那些放寒假的日子里,在外疯玩大半天后满头大汗地跑进伙房的我,忍着前胸贴后背的心慌慌,着急寻觅着灶台上外婆做好的菜肴,瞪大眼珠伸手从最诱惑的菜碗里拈出一小撮,高举着胳膊吊进嘴里,再陶醉地吧唧几下,咂咂舌,舔舔嘴,旋而侧转到添柴的灶口前,扒拉着吹火筒在灶堂里拨弄几趟,将外婆切好的糍粑小心塞搁进炉口,斜立在堂壁边耐火烘烤。
搓手等待糍粑成熟的过程中,我一边忍受着外婆的喋喋不休,眼睛却专注地盯着灶堂里的糍粑,守候着糍粑的肚子鼓胀起来。待糍粑烤好了,又小心地用火钳夹出来,扑哧扑哧吹去表面的灰土,捏着火烫的糍粑左手倒向右手,右手再倒往左手,边倒手边呼呼的吹气,生怕炙热的糍粑烫伤了手指。待糍粑余热微温,再龇牙咬去糍粑的一角,放出里面的热气,再塞填些佐味趁热大快朵颐地吞食起来。哪还顾得上理会外婆在一旁关切地笑骂,只是在歪着头得意地啃嚼糍粑时,嗯嗯无心应付着外婆的问话。偶尔侧头偷看外婆的一瞬,能发觉从她混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扶养孙儿长大了后的欣慰和幸福。
外婆陶醉于孙辈的淘气,总会想方设法地弄些花样美食来讨好孙儿。往烧好的糍粑里灌些白糖,让我吃到入口即化的糖糍粑。从酱坛子里择选几根泡生姜灌进烧好的糍粑里,成就为酸辣可口的酱糍粑。糍粑裹上鸡蛋汁在锅里仔细的炕,两面炕得金黄后,撒上麻丝盐,成为最敬客的蛋煎糍粑。还有酒糟蛋花煮糍粑,豆皮青菜猪油糍粑汤……就连外婆在火盆边温烤她的小脚时,我们都会暂时占了她的火盆,支上铁架烤上几块糍粑。
外婆已经作古,家乡土灶后的主角已替换成我的母亲,可我生活在城里的孩子,却没多大机会学习烤糍粑的手艺了。现在的农村在慢慢褪化,曾经飘荡在村庄上空的炊烟,在人丁稀少的老家已经慢慢淡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留守老人已会操作的没有温暖的电气化。家乡记忆中远去的精彩,现在只能回味而不可复制,纵使回到老地方,也唯徒有物似人非的悲凉。
人烟不盛的乡村,也只有在糍粑的召唤下,才能将外出奔波的游子陆续迎归故里。一家人围着饭桌,说着悦耳的家乡话,咀嚼着深入灵魂的饭菜香,听着老母亲熟悉的唠叨,而寡言的老父则蹲坐塘火前,手里夹着半截烟卷,眯着小眼挑拨着塘堆中的碳火灰尘,耐心指导好奇的孙儿烧烤着糍粑,心满意足地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
农村人的情怀,宛如餐桌上的糍粑,纯朴而实在。糍粑滋养着农村人,一代又一代,哪怕就是走到天边,在风儿吹过来的故乡的云下,也能闻到熟悉的糍粑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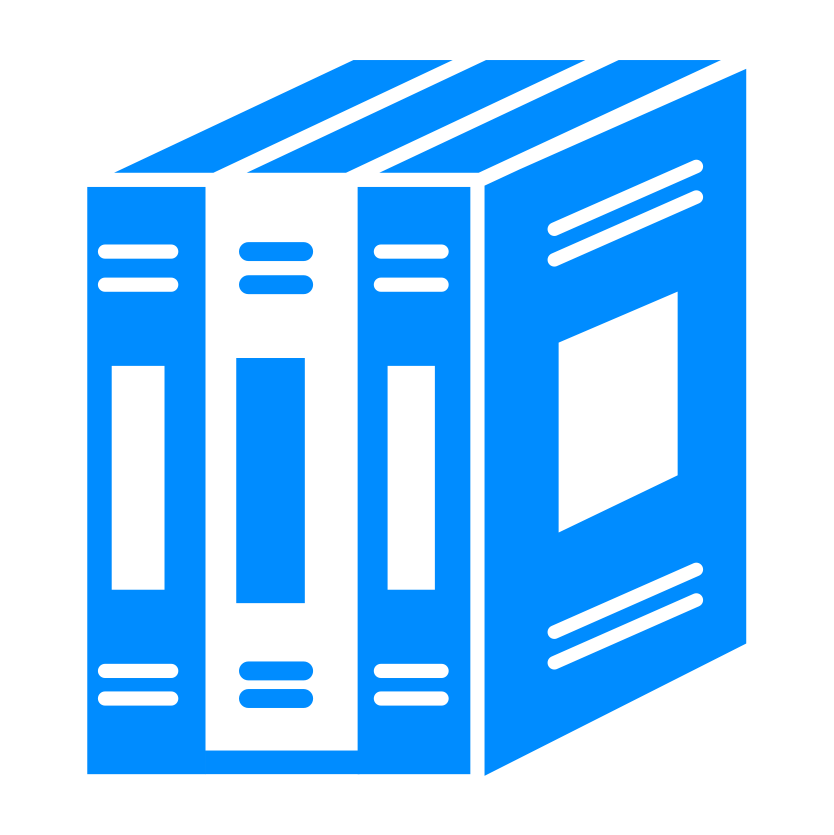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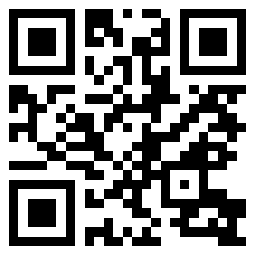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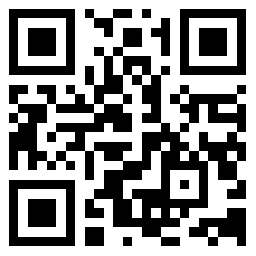
 微信收款码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