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事散文
叙事散文,以叙事为主,叙事情节不求完整,但很集中,叙事中的情渗透在字里行间。侧重于从叙述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反映事物的本质,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从一个角度选取题材,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根据散文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又可分为记事散文和写人散文。
-
窗前的漂游
窗前的漂游薄暮 打开窗,探身侧过脸,向西,能望见远处的虞山。山不算高,微微起伏,如一叶黛青色的柳眉。我原本住在那山脚下的城西,从乡村来到小城的二十几年里,有大半时间在此安家。搬了几次家,对家的概念越来越模糊,感觉只是一个栖息的窝,每一次乔迁……
-
城市边地【2】
在城市边地,车辆少了许多,即使横穿公路,也不需要长时间焦灼的等待。共享单车成了最好的交通工具。小区大门外一到傍晚就会停集了很多的共享单车。人在路上走,会听到不同的口音,即使说话的人都在使用普通话,但口音的差异却还是能于细微处分辨出来的,有南……
-
变化的故事情节,恒古不变的孤独
变化的故事情节,恒古不变的孤独——看汤姆汉克斯《荒岛余生》文‖林小白三十岁之后,很难平心静气看完一部完整的电影。晚上回家和伊一起做饭,吃饭的间隙,找了这部电影,开始看。中途上了两次厕所,暂停,再按播放键,将它完整看完。好看的电影有一种张力,……
-
故乡的故事
故乡的故事故乡的一草一木,无不侵淫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故事。有温馨暖心的母爱,有严格如山的父爱,也有姐弟、兄弟情,情情在眼前、情情在心底。它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更历久弥新。春夏之交,妈妈菜园里的那棵老桑树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桑子,在阳光在发出……
-
建国六十年古辰州地随想曲(原创首发)
建国六十年古辰州地随想曲文/萍庭鹤(小序:此文当时乃为了应本地散文交流之用,因为不停修改,一直没有发布,直到现在抽空,才认真斟酌一遍,并发布之!为了对读者负责,拖了很长时间,见笑了!) 当九月的铃声响了近60年之后,这个桃李满树的季节在古辰……
-
隐匿在陇山深处
固关不见关。“朝霜侵汉草,流沙渡陇飞。一闻《流水曲》,行住两沾衣”。这是南北朝人写的《陇头送征客》。一片凄惶。在固关遥望陇山,自有一种云深不知处的感慨。元朝时固关叫故关,是从陇县西行翻越陇坂的第一站。在固关街头,同行的张老师讲,《永乐大典》……
-
《土地,农民的命根》(修改稿)
《土地,农民的命根》五月,多情的季节。金色的阳光,透过密匝匝的树叶射在顺子和楞子兄弟身上。田埂上,架子车的影子也越来越短。顺子直起腰,用镰把在后背上轻轻地敲了两下,对弟弟楞子说:“唉,种地真他妈的辛苦,一年到头,耕地、下种、化肥、农药、杂七……
-
井冈山下荷花香
剑鸿阳光似乎有一些重量,堆积在山谷里,让人在满眼生辉中有点轻微的眩晕感。我的目光追随一只白鹭从荷花丛里盘旋而起。有了起伏苍翠的山影做背景,白鹭飞行的姿势如此分明,像是舞台灯光下的舞蹈演员,六月的阳光在她翅尖闪耀。我在想,如果有白鹭同样的飞行……
-
回忆熊清元老师
上个月教师节前后,看到很多网友写怀念老师的文章。我也经常想起原来的老师,有的已经十几年没有见面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始学古代文学。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进来的是一个矮瘦的老人。他用带着方音却洪亮的普通话自我介绍说:“我姓熊,和楚国的国君是本家。……
-
玉兰花
玉兰花豆蔻枝头二月初二月,冷风里的玉兰花微立枝头,形若豆蔻,被细细的绒毛包裹,却又在那绒毛的顶端露出些许白或红色来。那白是汉白玉般的白,碧透玲珑,暗暗生香;那红是红玛瑙似的红,如女子的唇刚点了胭脂一般。细细观赏,还会发现自红与白色中透出的灵……
-
雪
雪四周如此的静谧,喧嚣的杂音停止了躁动,哦,下雪了!身边静的是如此的小心,仿佛万物都是为了聆听雪的声音,而雪落确是无声。雪落在冰冷的树枝上停了一下,又向下随风飘落,落在地上,不一会化掉了,变成流动的水,水入江河,雪也飘落于黑水之上,江水吞噬……
-
想念三毛
想念三毛
文/海伦
看到一篇《三毛有荷西》的文章,我立马放下手上活儿,细读。这位长发披面、赤脚行走在沙漠里的女子,是我青春岁月的耶利亚女郎。我记不得从哪里得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不休不眠,一个晚上读完了。这之后,对三毛的喜爱,如中了盅…… -
蓝色鸢尾与蓝月亮
一,凝思,是回忆的常见态势。记得简城鳌山的绿色植物,除了一片绿色的蓝花楹、一株结荚的合欢树,并没有什么奇特的。惊动我的,是那一垄蓝色鸢尾,像是天上掉下的一只长尾巴风筝,不知怎么一头栽落竹篱边。蓝色鸢尾。近来总是想到它,于是屡屡看到它。那一天……
-
故乡俨然是异乡
站在街头望故乡,故乡俨然是异乡。水云深处湖天阔,难诉相思任笔狂。 我曾经在网络与现实中,都碰到这样一件令我十分难堪的事:常常有文友在微信和QQ上,拟或是在与我直面交流时,冷不丁地这样来问我,他们说,明然先生,我们读了你很多的文字,总觉得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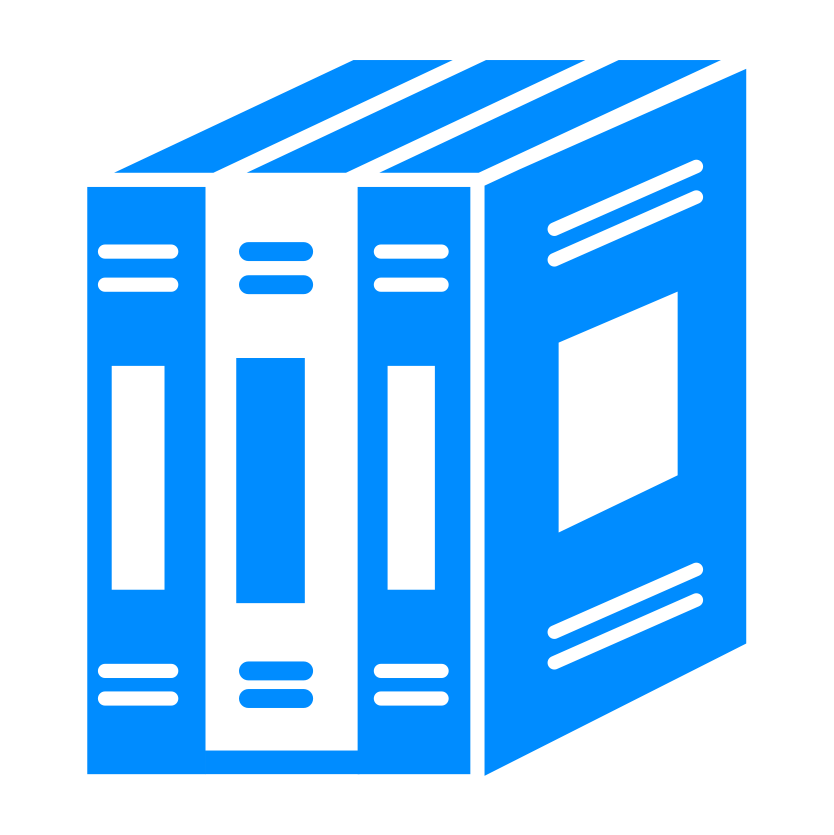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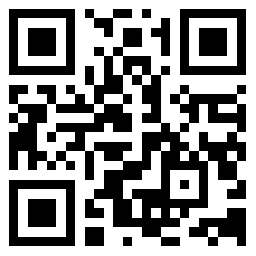
 微信收款码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