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重天
2025-06-14抒情散文陈草旭变
……
两 重 天
一
入夜九点,下楼消食散步,一如去年暑假的路线,在城中村里穿行。幽暗的灯光中,到处是酸腐腥臭的味道,步入熟悉的槐花小巷,依是少人,仲夏的夜晚,只有槐花槐香的记忆,浓郁的树荫里,有霓虹灯的远影,而腐朽味道依然盛行。绕过此横行的北归,是运粮河畔的岸路,几家还算整齐的二层楼房,却不见人家的活动,无风的夜空中,没有清流之声,一无水汽的净。
晨练在广场的西面一角,有高大繁荫的法桐,砌有菱形的台,围绕树根,可以坐人,背影中听到那有些艰涩的琴声。并不入群,背对行人的树台老人。那是自己常常站桩的地方,即便有风,也仍有腐败的味道,在那些草丛里弥散,不知是些什么腐朽的东西,在这盛热的夏季里发酵污浊。去之五十米外的几个法桐之下,我站桩打拳,空气好些,人并不多,却有几只苍蝇,追着我小腿的皮肤,复有瘙痒,被我一挥消灭,泛起微微的血腥。
附近小学到操场的路口,一弯石铺的小路,几棵不大却已成荫的柿树,六十平米左右,是可活动的幽静处所。地上以为是脏物的几般物什,收拾起是坠下的果实,已经腐烂,但没有腥臊。那小林路口有风,飒飒的一缕缕吹来,几乎吹散我站桩的定地定天定心的意念,吹散我头顶百会穴不断袅袅升起的息烟。那是心神可旷达而怡飞的所在,是不必到野外的河岸,不远足太阳落幕的西山,西山上的清风,还有那里清流的漱涤之声。
我的居家,我的“宁玥居”,就是这样的风口,一本书,一篇文章,更不比《登楼赋》之“建安七子”。复读第一遍,似气息于周身的又一次晨中往循,看一眼王桀的“登兹楼以四望兮”。高处有清风,远眺是清流,盛夏不避寒,而“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的清风之口,则是一座高楼。登高望远以沐风,处沐风以怡神。
人生清爽的风口?和谁与归?务农者,田畴傍晚的锄铲,阡陌晨兴的远眺,暮回门院的稳妥;经营人,晨起疏懒之际的开门酒洒,夜深客稀之时的往年小调。还有还有,虽“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但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可以糊涂呢?只是无奈而无奈,自知而自明吧。
选择放假开始的这种生活,也是自垒高台自择风口吧,柳宗元选溪之上游,“得其尤绝者家焉”。我所购置的运粮河畔的小区高楼,是否也是我内心的居所呢?如儿子没有能力购置新的居室,为其备用的高层正让于他了,但必要缓缓的告知,那高处的寒冷与爽怡,用十年的时间还完房贷,用二十年的时间告诉他清爽的高风,他可是同“三观”?可否能接受?而我,是否有二十年的天光?
二
昨夜雨,微微,雨丝之时,我步行胡同陋巷,隐隐绰绰,仿佛隔世,我则幽灵行走,观望着灯火阑珊的街头小店,店外的闲话,店头的桌椅,有一些欲邀好友夜话的冲动。但微微笑,知道已闭门不出。雨丝暂消,回家电视搜寻节目好久后,家人说又下雨,开窗伸手触摸,温度仍然未降,如此一夜酣睡,六点多自然醒来,出去晨练。
夜雨过后的街道,不熟悉的在西继大道之中北下一线,也有树荫,潮潮不宽的甬道上少有人行,停放的车辆,要等会儿有人开走上班,两辆大客照常停在许继公司的西面,车门洞开,司机在路旁的花圃边等待,应该是此公司去东区的公车。也是时代及此著名企业变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有同学在里,我的儿子去年的此夏,曾经我打工门卫。因此,步行过往,我看到门卫保安。
夜雨过后的五一路,最熟悉不过,高大的法桐,浓荫整个街道,对面走来的一个个妇人,大多是我的晚辈了。十七、八岁的法桐,三十年前常路此上学的途中,相伴至今,老树木了。而过马路之时,背北南眺,用我最深远沉静的目光,看到两行绿茵的南路,那景致竟然变得陌生,是我当年走过的街道吗?我上学的高中还在!潮湿洁净的大道,穿往远方的树荫,如此陌生,是另外的美域,尽管前面的处所及过往的时空,我皆知他们的在。
心情便在近十日的固守与修为中,达致我欲望的宁静而微微的愉悦,雨丝般的迷离,夜步行的自在,也看清楚,萦怀不去的关于友谊与同学等相交往的反思,不是某人某事,而是纠偏纠正,是修正修为,是舍弃扬弃,是自我的重新定位,正如你需要获取的舍弃,正是舍弃后的所得,便如此豁然,大多释然而平衡,平均而静谧的天空。
进取还是倒退?争与不争?比与不比?这是个辩证的问题。舍弃亦为获取,那么倒退固守,或者调整到原有的姿态,并非倒退,一如国策要独生子,现有鼓励二胎,依据的是大势的变化。那么,与何人争?与何人比呢?没有意义。应该是与自己争,与自己比,不必不争也是懦夫,与人相较竞争,不仅自不量力,徒增烦恼,也消耗了进取进步的精力不是,正如我高中时的自己,行道梧桐已经巨大成林,一路走来,已不枉过此生。
抑或是全方位辩证的比较与竞争。而这种胜与败的喜悲之处,也有统统罢手之后的安宁、不争,不为的宁静。正是人生需要一点儿,人生也得一点儿的甜。有荣光,必也有断肠。大抵如是。知道“大抵,咸为咸不为。”这一片海德格尔德的澄明之境。“在,在场,而澄明。”鬼使神差,上午的窗外,竟没有夏雨的信息,传来蝉叫和鸟鸣。
三
夜步到槐树下那鄙巷之际,又一次听到那排房后窗传来的播音声,是收音机播放的评书、歌曲,还有戏剧,有的是手机播放的吧。一排旧瓦屋,有五六个硕大的后窗,一窗为老人,一窗为中年,那一窗是个孩子,是个宅女吧,那些夏夜里,已不惧寂寞和闷热的“宅”。
如果“宅”那后窗,听到其内传来的悠悠声响,主人或躺或坐,或蒲扇,或读书,或家务吧,总归是幽静的,安宁的,我熟悉的那种。少年的暑假,会选了母亲的老屋,在水泥厂的家属院,铺了席子,阴凉的屋内,是两层的底层楼,光线阴郁,微亮从北窗而来,是桐荫滤过的明亮。卷席可以为榻,榻北角有两块干净的玻璃,青砖支起为矮桌,上有喜爱的图书画书,因其有席有桌为榻,安宁度越那休闲的少年时光。
那毕竟是家,是自己的空间吧。家庭变故的几年,居无定所,有了三楼的房间,自己以厨房为居室,虽只两平米大小,却一床一桌一墙柜,自己的天地,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和妻子结婚之后,那些暑假的时光,也是“宅”在那两平米的“书房”里,在无人的早晨,天刚刚亮的暑晨,才有时间出门,在院内子弟学校的杨树下,小凳读书,人多不来,方淡去归宅,那已经是另外的一番天地了。
到如今,有更大的房间,夜晚也不必非要卧在家里,听音乐看电视之类的,那外面广大的天地也是属于我的,可以走出去,游步于人来人往的街头,那些市声人声,就是清清新新的歌谣,优优雅雅的歌唱,独入其中的遥远的却又平近于身的评书或故事。夜晚并不黑暗,夜色闪烁的灯辉和可以挥之即去的人影。
白昼更是如此。晨练回来沐浴,简洁洗浴,水涤汗衫,吃早饭后,卷竹帘,铺凉台小书桌,读一遍昨天已学的《登楼赋》、《愚溪诗序》,查找准备的素材,《三国志》中一位将军出现的所有章节,段落与信息。同时送儿子我找的材料,准备午饭要做的辅料,更不用说下午发文章、写剧本的自由自在了。已经是另一种的天地,从房屋床榻,到肺腑心室;从夜色说唱,到此煌煌天光,两重天地。
一
入夜九点,下楼消食散步,一如去年暑假的路线,在城中村里穿行。幽暗的灯光中,到处是酸腐腥臭的味道,步入熟悉的槐花小巷,依是少人,仲夏的夜晚,只有槐花槐香的记忆,浓郁的树荫里,有霓虹灯的远影,而腐朽味道依然盛行。绕过此横行的北归,是运粮河畔的岸路,几家还算整齐的二层楼房,却不见人家的活动,无风的夜空中,没有清流之声,一无水汽的净。
晨练在广场的西面一角,有高大繁荫的法桐,砌有菱形的台,围绕树根,可以坐人,背影中听到那有些艰涩的琴声。并不入群,背对行人的树台老人。那是自己常常站桩的地方,即便有风,也仍有腐败的味道,在那些草丛里弥散,不知是些什么腐朽的东西,在这盛热的夏季里发酵污浊。去之五十米外的几个法桐之下,我站桩打拳,空气好些,人并不多,却有几只苍蝇,追着我小腿的皮肤,复有瘙痒,被我一挥消灭,泛起微微的血腥。
附近小学到操场的路口,一弯石铺的小路,几棵不大却已成荫的柿树,六十平米左右,是可活动的幽静处所。地上以为是脏物的几般物什,收拾起是坠下的果实,已经腐烂,但没有腥臊。那小林路口有风,飒飒的一缕缕吹来,几乎吹散我站桩的定地定天定心的意念,吹散我头顶百会穴不断袅袅升起的息烟。那是心神可旷达而怡飞的所在,是不必到野外的河岸,不远足太阳落幕的西山,西山上的清风,还有那里清流的漱涤之声。
我的居家,我的“宁玥居”,就是这样的风口,一本书,一篇文章,更不比《登楼赋》之“建安七子”。复读第一遍,似气息于周身的又一次晨中往循,看一眼王桀的“登兹楼以四望兮”。高处有清风,远眺是清流,盛夏不避寒,而“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的清风之口,则是一座高楼。登高望远以沐风,处沐风以怡神。
人生清爽的风口?和谁与归?务农者,田畴傍晚的锄铲,阡陌晨兴的远眺,暮回门院的稳妥;经营人,晨起疏懒之际的开门酒洒,夜深客稀之时的往年小调。还有还有,虽“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但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可以糊涂呢?只是无奈而无奈,自知而自明吧。
选择放假开始的这种生活,也是自垒高台自择风口吧,柳宗元选溪之上游,“得其尤绝者家焉”。我所购置的运粮河畔的小区高楼,是否也是我内心的居所呢?如儿子没有能力购置新的居室,为其备用的高层正让于他了,但必要缓缓的告知,那高处的寒冷与爽怡,用十年的时间还完房贷,用二十年的时间告诉他清爽的高风,他可是同“三观”?可否能接受?而我,是否有二十年的天光?
二
昨夜雨,微微,雨丝之时,我步行胡同陋巷,隐隐绰绰,仿佛隔世,我则幽灵行走,观望着灯火阑珊的街头小店,店外的闲话,店头的桌椅,有一些欲邀好友夜话的冲动。但微微笑,知道已闭门不出。雨丝暂消,回家电视搜寻节目好久后,家人说又下雨,开窗伸手触摸,温度仍然未降,如此一夜酣睡,六点多自然醒来,出去晨练。
夜雨过后的街道,不熟悉的在西继大道之中北下一线,也有树荫,潮潮不宽的甬道上少有人行,停放的车辆,要等会儿有人开走上班,两辆大客照常停在许继公司的西面,车门洞开,司机在路旁的花圃边等待,应该是此公司去东区的公车。也是时代及此著名企业变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有同学在里,我的儿子去年的此夏,曾经我打工门卫。因此,步行过往,我看到门卫保安。
夜雨过后的五一路,最熟悉不过,高大的法桐,浓荫整个街道,对面走来的一个个妇人,大多是我的晚辈了。十七、八岁的法桐,三十年前常路此上学的途中,相伴至今,老树木了。而过马路之时,背北南眺,用我最深远沉静的目光,看到两行绿茵的南路,那景致竟然变得陌生,是我当年走过的街道吗?我上学的高中还在!潮湿洁净的大道,穿往远方的树荫,如此陌生,是另外的美域,尽管前面的处所及过往的时空,我皆知他们的在。
心情便在近十日的固守与修为中,达致我欲望的宁静而微微的愉悦,雨丝般的迷离,夜步行的自在,也看清楚,萦怀不去的关于友谊与同学等相交往的反思,不是某人某事,而是纠偏纠正,是修正修为,是舍弃扬弃,是自我的重新定位,正如你需要获取的舍弃,正是舍弃后的所得,便如此豁然,大多释然而平衡,平均而静谧的天空。
进取还是倒退?争与不争?比与不比?这是个辩证的问题。舍弃亦为获取,那么倒退固守,或者调整到原有的姿态,并非倒退,一如国策要独生子,现有鼓励二胎,依据的是大势的变化。那么,与何人争?与何人比呢?没有意义。应该是与自己争,与自己比,不必不争也是懦夫,与人相较竞争,不仅自不量力,徒增烦恼,也消耗了进取进步的精力不是,正如我高中时的自己,行道梧桐已经巨大成林,一路走来,已不枉过此生。
抑或是全方位辩证的比较与竞争。而这种胜与败的喜悲之处,也有统统罢手之后的安宁、不争,不为的宁静。正是人生需要一点儿,人生也得一点儿的甜。有荣光,必也有断肠。大抵如是。知道“大抵,咸为咸不为。”这一片海德格尔德的澄明之境。“在,在场,而澄明。”鬼使神差,上午的窗外,竟没有夏雨的信息,传来蝉叫和鸟鸣。
三
夜步到槐树下那鄙巷之际,又一次听到那排房后窗传来的播音声,是收音机播放的评书、歌曲,还有戏剧,有的是手机播放的吧。一排旧瓦屋,有五六个硕大的后窗,一窗为老人,一窗为中年,那一窗是个孩子,是个宅女吧,那些夏夜里,已不惧寂寞和闷热的“宅”。
如果“宅”那后窗,听到其内传来的悠悠声响,主人或躺或坐,或蒲扇,或读书,或家务吧,总归是幽静的,安宁的,我熟悉的那种。少年的暑假,会选了母亲的老屋,在水泥厂的家属院,铺了席子,阴凉的屋内,是两层的底层楼,光线阴郁,微亮从北窗而来,是桐荫滤过的明亮。卷席可以为榻,榻北角有两块干净的玻璃,青砖支起为矮桌,上有喜爱的图书画书,因其有席有桌为榻,安宁度越那休闲的少年时光。
那毕竟是家,是自己的空间吧。家庭变故的几年,居无定所,有了三楼的房间,自己以厨房为居室,虽只两平米大小,却一床一桌一墙柜,自己的天地,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和妻子结婚之后,那些暑假的时光,也是“宅”在那两平米的“书房”里,在无人的早晨,天刚刚亮的暑晨,才有时间出门,在院内子弟学校的杨树下,小凳读书,人多不来,方淡去归宅,那已经是另外的一番天地了。
到如今,有更大的房间,夜晚也不必非要卧在家里,听音乐看电视之类的,那外面广大的天地也是属于我的,可以走出去,游步于人来人往的街头,那些市声人声,就是清清新新的歌谣,优优雅雅的歌唱,独入其中的遥远的却又平近于身的评书或故事。夜晚并不黑暗,夜色闪烁的灯辉和可以挥之即去的人影。
白昼更是如此。晨练回来沐浴,简洁洗浴,水涤汗衫,吃早饭后,卷竹帘,铺凉台小书桌,读一遍昨天已学的《登楼赋》、《愚溪诗序》,查找准备的素材,《三国志》中一位将军出现的所有章节,段落与信息。同时送儿子我找的材料,准备午饭要做的辅料,更不用说下午发文章、写剧本的自由自在了。已经是另一种的天地,从房屋床榻,到肺腑心室;从夜色说唱,到此煌煌天光,两重天地。
很赞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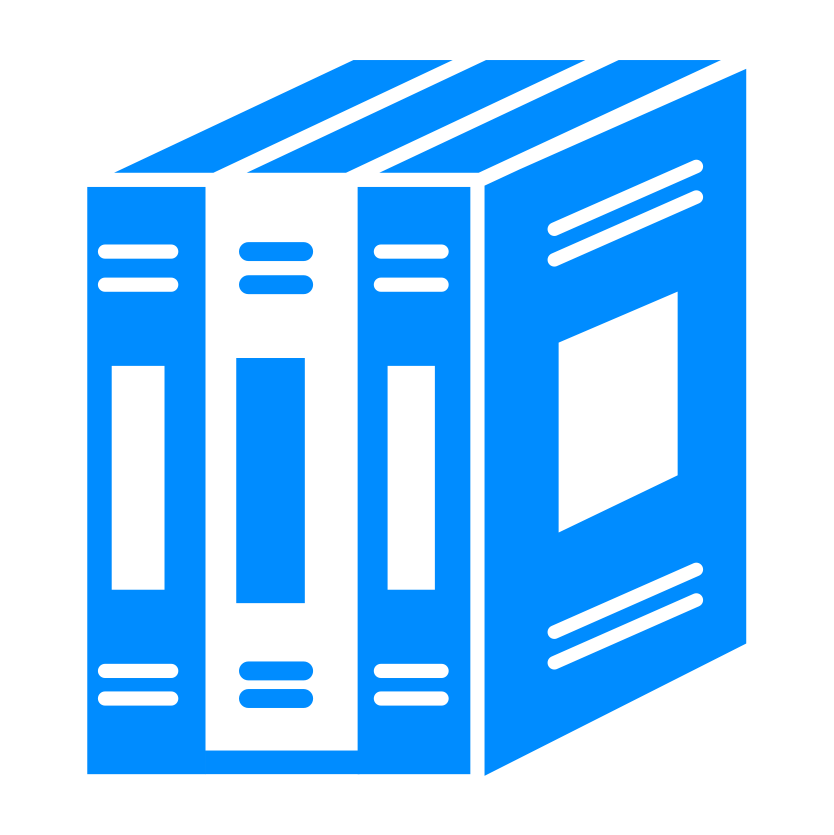



 微信收款码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