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北高楼(上)
2025-07-29抒情散文
此情可待成追忆……
序言
我于20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在山东省鲁西南广袤平原上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村落---北高楼。从孩提时代有记忆开始,我对这个懵懵懂懂的世界就充满了好奇与探索,在接下来几十年的经历中,我尝尽了人间的喜悦与悲情,相逢与离别,憧憬与迷茫。当然,还有一直无法忘却的回忆碎片时时敲打我的门窗,让我难以释怀。当我闲暇之余追忆成文,这又似一颗颗珍珠般珍贵,成为我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透过斑驳树影落下来的阳光似梦似烟尘。追忆似水流年,有些虚无缥缈;又恰似一江春水永驻我心,此情可待成追忆,平芜尽处是春山!
从记忆最初萌发的芽尖开始,这方天地便向我袒露了它朴素而神秘的胸膛。我如同一株新生的幼苗,带着未谙世事的懵懂与饥渴,每一寸肌肤、每一缕呼吸都浸润在黄土的气息里,向这混沌初开的世界伸出稚嫩而热切的触角,满心满眼皆是好奇的探寻与不倦的探索。
童年,那真是一段被阳光浸透、被大地稳稳承托的时光。村口那棵虬枝盘曲的老槐树,是季节轮转的忠实守望者。春日,它绽开一树细碎白花,清甜的香气在暖风里弥漫,引得成群的蜜蜂嗡嗡嘤嘤,织成一片朦胧的景象。我们这些孩子,赤着脚丫,在树下铺陈的绿荫里追逐嬉闹,笑声撞在老树干上,又清脆地弹回。夏日的午后,蝉鸣如潮水般汹涌,大地蒸腾着麦收后特有的、混合着泥土与新草的气息,灼热得仿佛空气本身也在燃烧。我们便如灵活的小鱼儿,一头扎进村后那条温润的小河里。河水被烈日烘烤得微温,清澈见底,卵石在脚底温柔地按摩。我们拍打着水花,追逐着偶尔掠过水面的翠鸟影子,那无拘无束的欢腾,仿佛能挣脱地心引力,直飞向天空深处。
冬春之交,则是另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旷野坦荡无垠,风从黄河故道裹挟着沙尘,无遮无拦地横扫过来,呜呜地撞击着低矮的土坯房檐,如同古老大地深沉的叹息。风沙拍打着窗棂,发出细密而持久的声响,仿佛无数细小的砂砾在低语。屋内,灶膛里的火苗跳跃着,映红了土炕的一角,温暖而踏实。窗外,天地一片混沌苍黄,风声灌满了耳朵。我蜷在父母温暖的炕头,听他们絮絮叨叨那些被风沙淘洗过无数遍的古老传说,故事里神仙的影影绰绰与窗外风沙的呼啸相互应和,织成一种奇异而安宁的童年底色。这风沙,这暖炕,这传说,共同熬煮着我最初感知世界的那碗浓汤,滋味粗粝又醇厚。
然而,如同所有离巢的鸟儿终要独自面对风雨,我终究告别了这方被老槐树荫蔽、被小河环绕、被风沙磨砺的故土,转身投入了时代的洪流。故乡温厚的土地在身后迅速坍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庞大、冰冷、喧嚣的陌生丛林。高楼如钢铁浇筑的峭壁,切割着被霓虹染红的天空;街道上,车流永不停歇,汇成一条条金属与噪音的河流,冰冷地冲刷着一切;人潮涌动,面孔模糊,步履匆匆,彼此擦肩而过,却如同隔着无形的、厚重的玻璃幕墙。最初的新鲜感如朝露般迅速蒸发,一种深重的荒凉与无法言说的孤独,如同冰冷的藤蔓,悄然缠绕上心头,在每一次黄昏降临、华灯初上之际,勒得人隐隐作痛。在这宏大的、高速运转的机器内部,生存便是一场艰难的角力。我学着收敛起少年时田野赋予的棱角与锋芒,将那些曾如野草般自由疯长的梦想,小心翼翼地折叠、压缩,努力熨帖成一张张打印纸所能容纳的规整模样。为了获得一个安放躯壳的格子间,为了换取几张维持体面的纸片,我笨拙地模仿着都市丛林里的生存法则,在觥筹交错的迷阵中跌跌撞撞,在人情世故的冰层上战战兢兢地行走。人间的喜悦,有时如电光石火,瞬间照亮晦暗;而悲情与离别,却如同无声的潮水,一次次漫过堤岸,在心底留下咸涩的淤痕。憧憬与迷茫交织缠绕,如同浓雾弥漫的清晨,看不清前路,也模糊了来处。异乡的灯火再璀璨,也总感觉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薄霜,那光芒无法真正抵达心底深处那个被乡音和土灶烘烤过的角落。
正是在这巨大的喧嚣与深刻的疏离中,那些早已沉淀在岁月河床之下的故乡碎片,却仿佛获得了新的生命,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它们不再是遥远的背景,而是化身为固执的访客,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或在城市匆忙的间隙悄然前来,“笃、笃、笃”地敲打我的心门。或许是某个清晨,窗外飘来一缕柴草燃烧的气息,竟瞬间击穿了都市的壁垒,将我猛地拉回童年灶膛前,母亲映着火光、被汗水微微濡湿的鬓角清晰如昨;或许是在地铁拥挤的人潮里,一个陌生老人浑浊而温和的眼神,倏然叠印在村头父亲满是沟壑的脸上;又或许,仅仅是一阵风过,卷起街角的尘土,那气息竟神奇地唤醒了鲁西南春天里,裹挟着麦苗清香的黄沙扑面的记忆……这些碎片如此鲜明,带着故乡泥土的温度和阳光的重量,它们不期而至,敲打着,提醒着,让我在都市的迷宫里一次次蓦然回首,心头涌起难以言喻的酸楚与暖意,久久难以释怀。
于是,当案牍劳形暂歇,当城市的声浪稍息,我便在属于自己的片刻闲暇里,尝试着将这些敲打心门的记忆碎片一一拾起,安放于草纸之上。这过程竟如同在时光的河滩上俯身,耐心地捡拾一颗颗被水流冲刷磨砺得温润的珍珠。每一颗珍珠,都封存着一段过往的光影,一缕特定的气息,一声被岁月模糊了的呼唤。写作,便是用文字的丝线将它们小心地串联,当它们最终在纸页上成串,在灯下散发出柔和而内敛的光泽时,我才恍然这并非简单的怀旧。它们已内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支撑我在异乡跋涉时,精神深处难以割舍的基石。透过这些文字望去,往昔的光阴,恰似穿透故乡庭院里那棵老槐树层层叠叠枝叶的斑驳阳光,明亮与幽暗交织,清晰与朦胧并存,如梦似幻,如烟似尘。它既真实可触,又带着一种无法完全把握的、流逝本身的忧伤。
追忆这似水流年,确乎常感其虚无缥缈,仿佛指尖流沙,握得越紧流逝越快。然而,它又绝非虚幻的泡影。那些沉淀下来的情感与记忆,那些被时间反复淘洗而愈发清晰的瞬间,早已汇集成一江春水,在我生命的河道里不息地流淌。它滋养着我,也冲刷着我,成为内心恒定的背景音。无论行至何方,遭遇何种境况,这江春水始终涌动,承载着故乡的倒影,映照着最初的来路。“此情可待成追忆”---这份情愫,这份对生命来处的深切凝视与回望,正是我提笔的内在驱动。“平芜尽处是春山”更如同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跋涉者的心境:纵然眼前是荒芜的旷野,步履沉重,但只要心怀对那方精神春山的笃信,坚持前行,翻过命运的山峦,希望的葱茏终会在视野尽头豁然展现。
这部小小的散文集,便是我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试图盛放那“斑驳树影落下阳光”的容器。它收集故乡灶膛里跳跃的火苗,收集小河里溅起的清凉水花,收集风沙中老槐树的低语,也收集城市迷宫中孤独的梵音、疲惫的叹息以及那些被现实擦伤后结痂的印记。它试图拼接那些不断敲打门窗的记忆碎片,将它们安放在文字的殿堂里,让瞬间的微光得以永恒。
倘若亲爱的读者,在这些粗疏的文字间穿行时,能偶尔驻足于某个段落、某个意象前,心弦被轻轻拨动---仿佛在纸页的反光里,也认出了属于你自己童年的那一缕炊烟,属于你奔波途中曾驻足回望的那片田野,或是属于你内心深处同样珍藏的朴素温暖---那么,这本小书便实现了它最珍贵的意义。它证明在各自孤寂的寒夜里,我们灵魂深处那不灭的心火,曾以文字为信使,隔着时空的荒野彼此辨认,遥遥致意。那些最珍贵的烟尘与光影, 传递着无声的慰藉:我们并不全然孤独,人生依然美丽如初。
第一部:此情可待成追忆
01捉白鲢鱼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天生对各种小动物充满了喜欢与好奇。离我们家很近的地方有两个水塘,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两个水塘之间有一条小水沟相连,听大人说两个水塘都有2~3米深,全村一年四季的雨水都储存在这里了。水塘里养了很多鱼儿,有草鱼,鲤鱼,鲶鱼等,其中以白鲢鱼最多。那个时代还是人民公社的时候,鱼儿归生产队,不属于个人,所以不允许社员私自钓鱼或者下水扑鱼。当然这些规定都是限制大人的,小孩子可管不了那么多。夏日炎炎的时候,成年人吃过午饭还不到下地劳动的时候,就会聚在水塘旁边的柳树下。有人铺一张席子,拿一个蒲扇盖在脸上纳凉睡觉,还有一些人搬来一个方桌,三五成群的围在一起打牌,那时候玩牌最多的叫“三五反”,四个人打的热火朝天,周围还有加油出主意的,吆喝声不断,好不热闹啊。当然,还有人摆一副象棋或者是军旗,杀得天昏地暗。还有人直接在地上画一个棋盘,双方用小石头子和木棍作棋子,玩“二顶一”的游戏。那时候人们的娱乐活动不多,这些就算是给平淡生活的调味品了。孩子们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们大多是下水塘游泳,三四岁的小孩都敢下,慢慢的自己就学会戏水了,只是家里的大人在旁边盯紧一些罢了,所以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几乎都会游泳,不像现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还要专门报游泳班学游泳,学不会的就成了旱鸭子,长大了就更不敢下水了。
那时候我还小,只有5~6岁吧,我的两个哥哥大概10~11岁的样子,他们经常在不去上学的时候带我在两个水塘相连的水沟里玩,水沟里的水大概齐腰深,基本上淹不了水。我的哥哥是附近有名的孩子王,他俩个都很聪明,从附近找来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棍横搭在水沟的两沿上,固定好木棍的两头。然后把我抱上去,让我骑在木棍上,双脚放在水里扑腾水花玩。其他小伙伴看到好玩,也纷纷加入我们的队伍,大家嘻嘻哈哈,把水沟里的水搅得水花四溅,混作一片。正在大家玩的兴起的时候,一条大白鲢鱼突然从小水塘里窜出水面,高高跃起从我们头顶飞过去,落在旁边的大池塘里,很快就消失了。我们都很兴奋,想着如果能捉住这条又大又好看的白鲢鱼该多好啊,这时候哥哥灵机一动,对大家说:“你们想不想捉鱼?”,
我们都齐声答应:“想啊,想啊!”
哥哥说:“想捉白鲢鱼也不难,白鲢鱼最怕动静,也不喜欢浑浊的水,我们几个大伙伴去小水塘,大家在里面把水搅浑,白鲢鱼肯定会沿着水沟往大水塘里跑,这时候你们小孩就站在木棍旁边,并排站好,使劲的来回摆腿,不让白鲢鱼过去,它们走投无路以后就会选择跳出水面,你们拿着木筐,等鱼儿跳起来的时候就用木筐接住,好不好?”
我们一听都拍手说好,大家说干就干,纷纷从家里拿来了木筐和水桶,一切准备就绪,哥哥一声令下,水性好的大孩子们就跟着他跳到小水塘里,他们在里面尽力扑腾,不一会儿功夫,就看到有鱼儿朝水沟这边游动过来,岸上的小伙伴大声说:“快看,快看,鱼儿游过来了”。
我们几个站在木棍旁边的小孩便开始使劲抖动腿,不让鱼儿游过去,这样来来回回几次,有些鱼儿就开始跳起来,从我们头顶和身边飞过去,哥哥一看机会来了,就大声说:“把木筐举起来逮鱼啊!”
我们就手忙脚乱的拿着木筐去罩鱼,有些鲤鱼儿很聪明,看着我们举着木筐就躲开了,还有的白鲢鱼很灵活,即使不小心落入木筐里也会很快就又跳出来,一眨眼的功夫跳进水里就不见了,我们忙活了半天也没有抓住一条鱼儿。大家虽然玩的不亦乐乎,但没抓住鱼还是有些失望,这时哥哥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我有新办法来了!”
他说完话就跑回家了,大家正在迟疑的时候,大老远的看见哥哥抱着一个大棉布包袱跑回来了,他把包袱铺开,安排我们四个小孩每人抓住一个角,然后大家下到水沟里,他说:“你们再看到鱼儿飞过来,就用大包袱裹住它,让它插翅难逃!”我们纷纷点头答应,果然这个方法很有效,一会儿功夫就逮到了几条白鲢鱼儿,一个个的又大又漂亮。大家玩的热火朝天的,不知不觉天就快要黑了,我们从水塘里爬出来,数数一共捉住十几条鱼儿,大家高兴极了,然后哥哥开始给大家按照人头分鱼,小伙伴们都乐开了花,心里想着今年晚上可以改善伙食了,吃一顿美美的炖鱼汤该多好啊!
农村的夜晚凉风习习,我和哥哥们闻着父母炖鱼的香味不时地飘进鼻子里,都禁不住喜笑颜开,我们吃着鲜美的鱼儿,喝着浓浓的鱼汤,水里别提多畅快了!
这件事情一转眼过去几十年了,直到现在,我还时时回忆起和哥哥扑鱼的场景,那些欢乐的瞬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想我再也回不到那快乐的童年了,再也无法重温那无忧无虑的日子,而且是再也吃不到那晚的美味了!
02放羊
我小时候最喜欢放羊,几乎每天都会跟着生产队里两位老爷爷去大洼的河沟里放羊。那时候放羊是集体的事情,每天早饭后,大家就把自家的羊赶到大队部的院子里,有小孩子就让小孩跟着,没有孩子的就托付给两位老爷爷。大部分羊是不需要做记号的,因为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街坊邻居,大家相互都熟悉的很,不会领错羊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所以经常和小伙伴们跟着去放羊,我们每个小孩手里都拿着一把小皮鞭,主要是赶羊用的。 我的小皮鞭是父亲帮我做的,他首先选一段粗细合适的柳树枝条,看下来剥掉外皮露出里面白色的木质,在木棍的顶端挖出一圈凹槽,拴上一米多长的麻绳,在麻绳的末端系上鞭梢,一个小皮鞭就做好了。一般来说鞭梢是用细的棉绳做的,鞭子甩起来响亮不响亮主要看鞭梢做的好不好,父亲会反复实验,直到我满意为止,另外为了小皮鞭好看,我还把鞭梢用红墨水染成红色,就更漂亮了。父亲还教给我怎么甩鞭子,他把鞭子拿在手里,先用力向空中一甩,紧接着一个回旋,鞭子在空中画出一个大大的“之”字形,就听到“啪”的一声,响彻天空。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甩起了鞭子,刚开始不得要领,鞭子发不出响声,后来父亲多次示范后我也就甩出响声来了。
我们这些小伙伴等所有的羊集合完毕,就跟着老爷爷赶着羊出发了,放养的地方在离村子很远的大洼里,那里河水清澈,绿草青青,是羊儿吃草的天堂。领头的羊是一只大公绵羊,头顶两个弯弯的羊角,体格健壮,个头比我们小孩子还要高,黄白色的毛发,头顶染成红色,走起路来威风凛凛的,相当炸裂。一般来说,领头羊是由一位老爷爷领着的,另外一位老爷爷在队伍的最后面,负责看管跟不上队伍的小羊。
我们去大洼的路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大道,两边都是社员的庄稼,我们赶羊的主要任务是看着羊不能让它们偷吃地里的庄稼。如果有羊不听话,我们就用鞭子甩出响声吓唬它或者直接上去抽打它,一路上几百只羊是不太好管理的,我们经常是走走停停,忙的不亦乐乎。不过大家都没觉得累,只是觉得好玩,羊儿一路欢叫,小孩子也一路吆喝,孩子们一个个笑脸迎着朝霞,煞是好看。终于把羊群赶到大洼里,羊儿撒欢的吃草,两位老爷爷也偷得半日闲暇,卧在草地上美美地抽上一袋烟,活似神仙般逍遥自在。远方蓝色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云儿这时候也扁的调皮起来,一会儿似羊、似牛似马儿,一会儿又像小孩子,真是美极了。我们小伙伴们就开始在草地里玩“撂骨碌”的游戏,实际上就是一对一摔跤。还有的孩子去捉蚂蚱或者蜻蜓,下河里摸青蛙。不知不觉中,羊儿们就吃饱了,它们就开始相互抵头角力,嬉戏玩耍。 尤其是一些比较强壮的大公羊想挑战领头羊的权威,就会和领头羊单挑,小孩子都喜欢看热闹,这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看看它们谁厉害?其中一只年轻力壮的大青羊非常高大,一身腱子肉外加一双大羊角非常拉风,它经常和领头羊决斗。只见它高高跃起,一头撞向领头羊,当然那只领头羊也好不客气,猛力一蹬,用双角迎击大青羊,只听“嘭”的一声,两只羊撞在了一起,大家都开始用力死死抵住对方,谁也不肯后退半步。我们这时候就分成两派,在旁边不断地为它们叫好加油,两只羊儿也好像是受到了鼓舞,干的更起劲了,大概一袋烟的功夫,那只大青羊终于坚持不住了,被领头羊顶了一个底朝天,落荒而逃了。我们就都鼓起了掌,领头羊虽然累的气喘吁吁,但是头高高昂起,向着天空“MIAN”的一声,响彻天空,就像一个得胜的将军在巡视自己的领地,想当霸气!
中午到了,我们开始返航,吃饱肚子的羊儿们不紧不慢,也不再调皮到处跑了,可是我们的肚子开始哇哇叫了,我们就加紧往家里赶。等回家后把羊儿关到羊圈里,我就在父母的催促下洗手吃饭,然后美美地睡个午觉去了。
03印娃娃模
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成长于八十年代,那时候的农村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地方,但是人们的脸上却经常挂着笑容,感觉生活有滋有味,有奔头。对于我们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是没有玩具可买的,即使有卖的也买不起,我们那时候玩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比如说娃娃模,四角板,手枪,弓箭等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动手制作娃娃模,每年的初夏来临之前,我和小伙伴下午放学后就从教室里直奔家里的小水沟,那时沟是干枯的,我们就沿着沟底寻找制作娃娃模的材料-一种粘性很大的黄胶土,我们又称它为“胶泥”。这种土质又有韧劲还有可塑性,最适合制作娃娃模。由于这种土质都是埋在松软的灰土下面,我们要挖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一旦找到大家都欢呼起来,每人挖一大块,放在书包里运到沟沿上,然后大家一起带着这些胶泥来到村口的大石头上,当时村口有几个雕字画龙的石碑,据说是清末有钱人家立的,解放后就被村民推倒了,放在村口路边的树荫下,人们在那里可以小坐纳凉。后来就成了我们小孩子制作娃娃模的专用地方了。那几个石碑表面光滑,又大又平整,我们把胶泥放在上面,我们从家里提一桶水,就可以制作娃娃模了。
制作娃娃模的工序比较简单,首先我们把泥土和水混合,然后把胶泥揉在一块,使劲的揉搓,就像家里和面一样,时不时的还要拿起泥块在石碑上摔几下,以增加它的柔韧性。直到我们把黄胶泥揉的圆圆的,光滑滑的,那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就开始拿出借来的模子制作了,这些模子是从高年级的同学那里借来的,估计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买的,只能借给我们一个晚上,明天上学时就得还回去,我猜是主人怕我们给它弄坏了,都比较珍贵吧,据说那些模子都是用土窑烧了三天三夜才出窑的,自然是十分昂贵,据说需要1元钱才能买到一个,根据货币换算,七十年代末的一元钱相当于现在的100元也不止吧,我们这些普通家里的孩子自然是买不起的。那时模子做的都很精美,有好多不同的系列,比如西游记系列,有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白骨精、海龙王等;还有水浒传系列,有武松、李逵、鲁智深、林冲等好汉形象。我们首先拿出一块小泥巴,把它摊平涂到模子里,然后使劲压实,让胶泥和模子完全贴合在一起,接着再压边,用树枝去掉周围多于的泥巴,放在那里过2分钟后,用手轻轻的把泥巴从模子里扣下来,动作一定要慢,千万不要把泥巴扣烂了,那样就前功尽弃了。等我们把胶泥扣下来以后,就可以看到一个模子的图案一样的娃娃模了。这时候都会很兴奋,高声吆喝起来,当然也有不成功的时候,比如胶泥揉的不到火候或者掺水太多,都有可能制作不成功,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推倒重做,不一会儿功夫,石碑上就摆满了我们制作的娃娃模。娃娃模接下来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等娃娃模晾干后,我们按照人头和个人喜好把娃娃模分了,然后各自带回家,放在各家屋顶上或者砖墙上,继续晒干,以后就可以拿着到处炫耀和玩耍了,但是这样处理的娃娃模容易干裂变脆,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碎了。还有一种方式是大家接着再加工,把娃娃模放在火炉上烤,火炉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首先找来几块砖,垒出一个灶来,再在上面搭一个又薄又平的石板,把刚刚制作好的娃娃模放在上面依次摆好,接着就找来木柴和干树枝点火,烤制娃娃模。大概用火烤两个小时候后,娃娃模就初步烧制成功了,这时候娃娃模大多变成金黄色,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非常漂亮。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不成功的,烧制出来的娃娃模一块青色一块黑色的,但是,我们也不舍得扔掉,因为那时候的玩具太匮乏了,又是自己亲手做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再丑也舍不得扔啊。
不知不觉中天就黑了,家里大人开始喊吃晚饭了,我们就把娃娃模分了各自放在书包里带回家去,那时候这些玩具大多是不敢让家里的大人看的,怕大人说我们在外面疯玩,不早点回家干活,我们都是偷偷的放在书包里带回家,等吃过晚饭就开始做作业了,那时候老师布置的作业非常少,不超过5个题目,二十分钟就能完成了,因为那时候上学除了课本基本上没有任何辅导书,老师手里也不过是比我们多了一本参考书而已,也不可能出多少题给我们,不想现在的小学生,课桌上堆的书比人都高,家里的书橱里也全是满满的辅导书,每天放学回家没有两个小时是处理不完作业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那时候的孩子是很幸福的,虽然物资很匮乏,但是童年很快乐,每个孩子的眼里都有光。再看看现在的孩子吧,他们虽然吃的好、玩的高级、玩具也很丰富,但是他们大多数活的很累、很卷,这样长大的孩子能幸福吗?
等到晚上睡觉时,大人劳累了一天很快就睡着了,这时候我躺在被窝里,把白天做好的娃娃模偷偷的拿出来,端详把玩很久,简直是爱不释手,最后实在困的不行了,才抱着娃娃模懵懂地睡去,我想晚上即使做梦也会笑醒吧。
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一个片段,已经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家里的房子里找寻那些娃娃模,随着几次搬迁、几次翻盖新房,估计是很难找到了,但关于娃娃模的记忆将永远伴随我的一生!
04摔泥巴
我在孩提时代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摔泥巴,夏季的中午,我每次放学回来以后,草草地扒拉几口饭,喝上一勺子凉水,就急着跑出去找小伙伴玩摔泥巴的游戏,泥巴是从水坑边上一块取回来的,然后大家每人等分一大块泥巴,大家找一个平坦的石头,像大人揉面一样用力在上面把泥巴揉揣,等泥巴变得柔韧不易散开时,我就把它做成一个大碗的形状,放在手上高高举起,碗口向下,用力摔在地面上,只听“嘭”的一声,泥巴碗的底面就出现一个类圆形的洞洞,琐碎的泥巴四处飞溅。另一个小伙伴就把自己的泥巴团成一个圆球,大小和洞的体积差不多,放在洞上就算把碗底补上了,这个用泥巴团成的圆球就是我的战利品,我把圆球和破碎的泥巴碗一块收起来,把它们捏合在一起,下次就可以做一个更大的碗。这时就该轮到我的小伙伴摔他的泥巴碗了,他摔出的洞我也必须拿自己的泥巴给他补上。然后就是下一轮比赛,看看谁摔出的洞洞大,谁就赢的泥巴多,这样几轮比赛下来,有的人手头的泥巴就会越来越少,而另一个手里的泥巴就会越来越多,最后当一方的泥巴补不上另一方摔出来的洞时,就算输了,输的一方就很泄气,赢的一方自然神气多了,就像打仗获胜的将军一样,这次游戏也就停止了。然后大家再重新等分泥巴一较高低。这个游戏虽然简单,但是大家却玩的不亦乐乎,脸上、手上和身上到处弄的都是泥巴,大家都不以为然,只是陶醉在儿时的争抢好胜里面,现在想想那时的孩子心里面真的很纯净,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一块小泥巴就能伴随我们快乐地长大,这也算是上天对我们农村孩子的馈赠吧!现在我和女儿谈起我摔泥巴的情形,她始终张大嘴巴,摆出一副不可置信的摸样,我知道她是怎么也不会理解我贫苦的童年里把一块脏兮兮的泥巴当做玩具而爱不释手的。她的世界里玩具都是从商场里或者网上购买的,玩的泥巴那也是用五颜六色的橡皮泥替代的,既干净又漂亮,价格
自然不低,而我那个时代花一角钱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大人是绝对不允许孩子把钱花在玩耍上面,那对我来说是多么奢侈的行为啊!
然而我现在还时时记起和小伙伴玩泥巴的场景,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时间是最不经用的,转眼已过半生。儿时的记忆渐渐模糊,但是甩泥巴的印记却越来越明晰,似乎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05做弹弓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打鸟玩,各种鸟类包括麻雀、咕咕鸟、大吗嘎子等,小燕子是不打的,据说是益虫。打鸟就必须先做弹弓,做弹弓的材料主要是弹弓架、橡皮筋和牛皮。弹弓架一般选用柳树的Y字形树枝,把外皮去掉,里面是雪白的木质材料,当然也可以选楝子树枝,那个更有柔韧性,只是不好遇到罢了。橡皮筋是越粗的越有劲,射程也越远,但是比较费力拉开。牛皮则是取来做包裹石子的拉手。弹弓的子弹主要是实用圆圆的石子或者是土坷垃,硬度要足够才能把鸟打下来。
制作弹弓的工序基本是这样的:首先是选取一个左右粗细基本对称的Y字形树枝,去掉尾部和左右的头部,做出一个近似Y字形来。然后在左右头部开个槽子,分别系好两根橡皮筋,两根橡皮筋的另外两端系在牛皮上,一个简单的弹弓就做好了。
我们一般喜欢在冬天的下午放学后去打鸟,因为冬天树叶都落了,小鸟藏在树上一眼就能看到,我们看到枝头的麻雀后就悄悄地溜到树下,左手举起弹弓,瞄准麻雀,右手使劲拉开皮筋,等确认准头以后松开手,石子“嗖”的一下就射出去了,如果运气好的话就打中了,小麻雀应声从树上掉下来,我们一拥而上把它抓住,放进准备好的口袋里。一般情况下是打不准的,忙活一下午也就能够打下来四五只。当然如果运气特别好也可以打到大吗嘎子,它是一种特别大的鸟,全身乌黑乌黑的。等到太阳落山,我们就找一个田间地头,挖一个简单的锅灶,找来干树枝点火烤小鸟吃,直到烤的呲呲冒油,我就开始品尝美味了,那种原始肉香的味道非常鲜美,尤其是在那个物质及其匮乏的时代。到现在还时时记起这种味道,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现在虽然也能出去吃到各种各样的烧烤,食材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再也不是小时候的那个感觉了,我想这不仅仅是没有以前的味道了,可能也是再也找不到儿时的玩伴在一起嬉闹开心的日子了。
我于20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在山东省鲁西南广袤平原上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村落---北高楼。从孩提时代有记忆开始,我对这个懵懵懂懂的世界就充满了好奇与探索,在接下来几十年的经历中,我尝尽了人间的喜悦与悲情,相逢与离别,憧憬与迷茫。当然,还有一直无法忘却的回忆碎片时时敲打我的门窗,让我难以释怀。当我闲暇之余追忆成文,这又似一颗颗珍珠般珍贵,成为我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透过斑驳树影落下来的阳光似梦似烟尘。追忆似水流年,有些虚无缥缈;又恰似一江春水永驻我心,此情可待成追忆,平芜尽处是春山!
从记忆最初萌发的芽尖开始,这方天地便向我袒露了它朴素而神秘的胸膛。我如同一株新生的幼苗,带着未谙世事的懵懂与饥渴,每一寸肌肤、每一缕呼吸都浸润在黄土的气息里,向这混沌初开的世界伸出稚嫩而热切的触角,满心满眼皆是好奇的探寻与不倦的探索。
童年,那真是一段被阳光浸透、被大地稳稳承托的时光。村口那棵虬枝盘曲的老槐树,是季节轮转的忠实守望者。春日,它绽开一树细碎白花,清甜的香气在暖风里弥漫,引得成群的蜜蜂嗡嗡嘤嘤,织成一片朦胧的景象。我们这些孩子,赤着脚丫,在树下铺陈的绿荫里追逐嬉闹,笑声撞在老树干上,又清脆地弹回。夏日的午后,蝉鸣如潮水般汹涌,大地蒸腾着麦收后特有的、混合着泥土与新草的气息,灼热得仿佛空气本身也在燃烧。我们便如灵活的小鱼儿,一头扎进村后那条温润的小河里。河水被烈日烘烤得微温,清澈见底,卵石在脚底温柔地按摩。我们拍打着水花,追逐着偶尔掠过水面的翠鸟影子,那无拘无束的欢腾,仿佛能挣脱地心引力,直飞向天空深处。
冬春之交,则是另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旷野坦荡无垠,风从黄河故道裹挟着沙尘,无遮无拦地横扫过来,呜呜地撞击着低矮的土坯房檐,如同古老大地深沉的叹息。风沙拍打着窗棂,发出细密而持久的声响,仿佛无数细小的砂砾在低语。屋内,灶膛里的火苗跳跃着,映红了土炕的一角,温暖而踏实。窗外,天地一片混沌苍黄,风声灌满了耳朵。我蜷在父母温暖的炕头,听他们絮絮叨叨那些被风沙淘洗过无数遍的古老传说,故事里神仙的影影绰绰与窗外风沙的呼啸相互应和,织成一种奇异而安宁的童年底色。这风沙,这暖炕,这传说,共同熬煮着我最初感知世界的那碗浓汤,滋味粗粝又醇厚。
然而,如同所有离巢的鸟儿终要独自面对风雨,我终究告别了这方被老槐树荫蔽、被小河环绕、被风沙磨砺的故土,转身投入了时代的洪流。故乡温厚的土地在身后迅速坍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庞大、冰冷、喧嚣的陌生丛林。高楼如钢铁浇筑的峭壁,切割着被霓虹染红的天空;街道上,车流永不停歇,汇成一条条金属与噪音的河流,冰冷地冲刷着一切;人潮涌动,面孔模糊,步履匆匆,彼此擦肩而过,却如同隔着无形的、厚重的玻璃幕墙。最初的新鲜感如朝露般迅速蒸发,一种深重的荒凉与无法言说的孤独,如同冰冷的藤蔓,悄然缠绕上心头,在每一次黄昏降临、华灯初上之际,勒得人隐隐作痛。在这宏大的、高速运转的机器内部,生存便是一场艰难的角力。我学着收敛起少年时田野赋予的棱角与锋芒,将那些曾如野草般自由疯长的梦想,小心翼翼地折叠、压缩,努力熨帖成一张张打印纸所能容纳的规整模样。为了获得一个安放躯壳的格子间,为了换取几张维持体面的纸片,我笨拙地模仿着都市丛林里的生存法则,在觥筹交错的迷阵中跌跌撞撞,在人情世故的冰层上战战兢兢地行走。人间的喜悦,有时如电光石火,瞬间照亮晦暗;而悲情与离别,却如同无声的潮水,一次次漫过堤岸,在心底留下咸涩的淤痕。憧憬与迷茫交织缠绕,如同浓雾弥漫的清晨,看不清前路,也模糊了来处。异乡的灯火再璀璨,也总感觉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薄霜,那光芒无法真正抵达心底深处那个被乡音和土灶烘烤过的角落。
正是在这巨大的喧嚣与深刻的疏离中,那些早已沉淀在岁月河床之下的故乡碎片,却仿佛获得了新的生命,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它们不再是遥远的背景,而是化身为固执的访客,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或在城市匆忙的间隙悄然前来,“笃、笃、笃”地敲打我的心门。或许是某个清晨,窗外飘来一缕柴草燃烧的气息,竟瞬间击穿了都市的壁垒,将我猛地拉回童年灶膛前,母亲映着火光、被汗水微微濡湿的鬓角清晰如昨;或许是在地铁拥挤的人潮里,一个陌生老人浑浊而温和的眼神,倏然叠印在村头父亲满是沟壑的脸上;又或许,仅仅是一阵风过,卷起街角的尘土,那气息竟神奇地唤醒了鲁西南春天里,裹挟着麦苗清香的黄沙扑面的记忆……这些碎片如此鲜明,带着故乡泥土的温度和阳光的重量,它们不期而至,敲打着,提醒着,让我在都市的迷宫里一次次蓦然回首,心头涌起难以言喻的酸楚与暖意,久久难以释怀。
于是,当案牍劳形暂歇,当城市的声浪稍息,我便在属于自己的片刻闲暇里,尝试着将这些敲打心门的记忆碎片一一拾起,安放于草纸之上。这过程竟如同在时光的河滩上俯身,耐心地捡拾一颗颗被水流冲刷磨砺得温润的珍珠。每一颗珍珠,都封存着一段过往的光影,一缕特定的气息,一声被岁月模糊了的呼唤。写作,便是用文字的丝线将它们小心地串联,当它们最终在纸页上成串,在灯下散发出柔和而内敛的光泽时,我才恍然这并非简单的怀旧。它们已内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支撑我在异乡跋涉时,精神深处难以割舍的基石。透过这些文字望去,往昔的光阴,恰似穿透故乡庭院里那棵老槐树层层叠叠枝叶的斑驳阳光,明亮与幽暗交织,清晰与朦胧并存,如梦似幻,如烟似尘。它既真实可触,又带着一种无法完全把握的、流逝本身的忧伤。
追忆这似水流年,确乎常感其虚无缥缈,仿佛指尖流沙,握得越紧流逝越快。然而,它又绝非虚幻的泡影。那些沉淀下来的情感与记忆,那些被时间反复淘洗而愈发清晰的瞬间,早已汇集成一江春水,在我生命的河道里不息地流淌。它滋养着我,也冲刷着我,成为内心恒定的背景音。无论行至何方,遭遇何种境况,这江春水始终涌动,承载着故乡的倒影,映照着最初的来路。“此情可待成追忆”---这份情愫,这份对生命来处的深切凝视与回望,正是我提笔的内在驱动。“平芜尽处是春山”更如同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跋涉者的心境:纵然眼前是荒芜的旷野,步履沉重,但只要心怀对那方精神春山的笃信,坚持前行,翻过命运的山峦,希望的葱茏终会在视野尽头豁然展现。
这部小小的散文集,便是我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试图盛放那“斑驳树影落下阳光”的容器。它收集故乡灶膛里跳跃的火苗,收集小河里溅起的清凉水花,收集风沙中老槐树的低语,也收集城市迷宫中孤独的梵音、疲惫的叹息以及那些被现实擦伤后结痂的印记。它试图拼接那些不断敲打门窗的记忆碎片,将它们安放在文字的殿堂里,让瞬间的微光得以永恒。
倘若亲爱的读者,在这些粗疏的文字间穿行时,能偶尔驻足于某个段落、某个意象前,心弦被轻轻拨动---仿佛在纸页的反光里,也认出了属于你自己童年的那一缕炊烟,属于你奔波途中曾驻足回望的那片田野,或是属于你内心深处同样珍藏的朴素温暖---那么,这本小书便实现了它最珍贵的意义。它证明在各自孤寂的寒夜里,我们灵魂深处那不灭的心火,曾以文字为信使,隔着时空的荒野彼此辨认,遥遥致意。那些最珍贵的烟尘与光影, 传递着无声的慰藉:我们并不全然孤独,人生依然美丽如初。
第一部:此情可待成追忆
01捉白鲢鱼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天生对各种小动物充满了喜欢与好奇。离我们家很近的地方有两个水塘,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两个水塘之间有一条小水沟相连,听大人说两个水塘都有2~3米深,全村一年四季的雨水都储存在这里了。水塘里养了很多鱼儿,有草鱼,鲤鱼,鲶鱼等,其中以白鲢鱼最多。那个时代还是人民公社的时候,鱼儿归生产队,不属于个人,所以不允许社员私自钓鱼或者下水扑鱼。当然这些规定都是限制大人的,小孩子可管不了那么多。夏日炎炎的时候,成年人吃过午饭还不到下地劳动的时候,就会聚在水塘旁边的柳树下。有人铺一张席子,拿一个蒲扇盖在脸上纳凉睡觉,还有一些人搬来一个方桌,三五成群的围在一起打牌,那时候玩牌最多的叫“三五反”,四个人打的热火朝天,周围还有加油出主意的,吆喝声不断,好不热闹啊。当然,还有人摆一副象棋或者是军旗,杀得天昏地暗。还有人直接在地上画一个棋盘,双方用小石头子和木棍作棋子,玩“二顶一”的游戏。那时候人们的娱乐活动不多,这些就算是给平淡生活的调味品了。孩子们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们大多是下水塘游泳,三四岁的小孩都敢下,慢慢的自己就学会戏水了,只是家里的大人在旁边盯紧一些罢了,所以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几乎都会游泳,不像现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还要专门报游泳班学游泳,学不会的就成了旱鸭子,长大了就更不敢下水了。
那时候我还小,只有5~6岁吧,我的两个哥哥大概10~11岁的样子,他们经常在不去上学的时候带我在两个水塘相连的水沟里玩,水沟里的水大概齐腰深,基本上淹不了水。我的哥哥是附近有名的孩子王,他俩个都很聪明,从附近找来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棍横搭在水沟的两沿上,固定好木棍的两头。然后把我抱上去,让我骑在木棍上,双脚放在水里扑腾水花玩。其他小伙伴看到好玩,也纷纷加入我们的队伍,大家嘻嘻哈哈,把水沟里的水搅得水花四溅,混作一片。正在大家玩的兴起的时候,一条大白鲢鱼突然从小水塘里窜出水面,高高跃起从我们头顶飞过去,落在旁边的大池塘里,很快就消失了。我们都很兴奋,想着如果能捉住这条又大又好看的白鲢鱼该多好啊,这时候哥哥灵机一动,对大家说:“你们想不想捉鱼?”,
我们都齐声答应:“想啊,想啊!”
哥哥说:“想捉白鲢鱼也不难,白鲢鱼最怕动静,也不喜欢浑浊的水,我们几个大伙伴去小水塘,大家在里面把水搅浑,白鲢鱼肯定会沿着水沟往大水塘里跑,这时候你们小孩就站在木棍旁边,并排站好,使劲的来回摆腿,不让白鲢鱼过去,它们走投无路以后就会选择跳出水面,你们拿着木筐,等鱼儿跳起来的时候就用木筐接住,好不好?”
我们一听都拍手说好,大家说干就干,纷纷从家里拿来了木筐和水桶,一切准备就绪,哥哥一声令下,水性好的大孩子们就跟着他跳到小水塘里,他们在里面尽力扑腾,不一会儿功夫,就看到有鱼儿朝水沟这边游动过来,岸上的小伙伴大声说:“快看,快看,鱼儿游过来了”。
我们几个站在木棍旁边的小孩便开始使劲抖动腿,不让鱼儿游过去,这样来来回回几次,有些鱼儿就开始跳起来,从我们头顶和身边飞过去,哥哥一看机会来了,就大声说:“把木筐举起来逮鱼啊!”
我们就手忙脚乱的拿着木筐去罩鱼,有些鲤鱼儿很聪明,看着我们举着木筐就躲开了,还有的白鲢鱼很灵活,即使不小心落入木筐里也会很快就又跳出来,一眨眼的功夫跳进水里就不见了,我们忙活了半天也没有抓住一条鱼儿。大家虽然玩的不亦乐乎,但没抓住鱼还是有些失望,这时哥哥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我有新办法来了!”
他说完话就跑回家了,大家正在迟疑的时候,大老远的看见哥哥抱着一个大棉布包袱跑回来了,他把包袱铺开,安排我们四个小孩每人抓住一个角,然后大家下到水沟里,他说:“你们再看到鱼儿飞过来,就用大包袱裹住它,让它插翅难逃!”我们纷纷点头答应,果然这个方法很有效,一会儿功夫就逮到了几条白鲢鱼儿,一个个的又大又漂亮。大家玩的热火朝天的,不知不觉天就快要黑了,我们从水塘里爬出来,数数一共捉住十几条鱼儿,大家高兴极了,然后哥哥开始给大家按照人头分鱼,小伙伴们都乐开了花,心里想着今年晚上可以改善伙食了,吃一顿美美的炖鱼汤该多好啊!
农村的夜晚凉风习习,我和哥哥们闻着父母炖鱼的香味不时地飘进鼻子里,都禁不住喜笑颜开,我们吃着鲜美的鱼儿,喝着浓浓的鱼汤,水里别提多畅快了!
这件事情一转眼过去几十年了,直到现在,我还时时回忆起和哥哥扑鱼的场景,那些欢乐的瞬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想我再也回不到那快乐的童年了,再也无法重温那无忧无虑的日子,而且是再也吃不到那晚的美味了!
02放羊
我小时候最喜欢放羊,几乎每天都会跟着生产队里两位老爷爷去大洼的河沟里放羊。那时候放羊是集体的事情,每天早饭后,大家就把自家的羊赶到大队部的院子里,有小孩子就让小孩跟着,没有孩子的就托付给两位老爷爷。大部分羊是不需要做记号的,因为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街坊邻居,大家相互都熟悉的很,不会领错羊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所以经常和小伙伴们跟着去放羊,我们每个小孩手里都拿着一把小皮鞭,主要是赶羊用的。 我的小皮鞭是父亲帮我做的,他首先选一段粗细合适的柳树枝条,看下来剥掉外皮露出里面白色的木质,在木棍的顶端挖出一圈凹槽,拴上一米多长的麻绳,在麻绳的末端系上鞭梢,一个小皮鞭就做好了。一般来说鞭梢是用细的棉绳做的,鞭子甩起来响亮不响亮主要看鞭梢做的好不好,父亲会反复实验,直到我满意为止,另外为了小皮鞭好看,我还把鞭梢用红墨水染成红色,就更漂亮了。父亲还教给我怎么甩鞭子,他把鞭子拿在手里,先用力向空中一甩,紧接着一个回旋,鞭子在空中画出一个大大的“之”字形,就听到“啪”的一声,响彻天空。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甩起了鞭子,刚开始不得要领,鞭子发不出响声,后来父亲多次示范后我也就甩出响声来了。
我们这些小伙伴等所有的羊集合完毕,就跟着老爷爷赶着羊出发了,放养的地方在离村子很远的大洼里,那里河水清澈,绿草青青,是羊儿吃草的天堂。领头的羊是一只大公绵羊,头顶两个弯弯的羊角,体格健壮,个头比我们小孩子还要高,黄白色的毛发,头顶染成红色,走起路来威风凛凛的,相当炸裂。一般来说,领头羊是由一位老爷爷领着的,另外一位老爷爷在队伍的最后面,负责看管跟不上队伍的小羊。
我们去大洼的路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大道,两边都是社员的庄稼,我们赶羊的主要任务是看着羊不能让它们偷吃地里的庄稼。如果有羊不听话,我们就用鞭子甩出响声吓唬它或者直接上去抽打它,一路上几百只羊是不太好管理的,我们经常是走走停停,忙的不亦乐乎。不过大家都没觉得累,只是觉得好玩,羊儿一路欢叫,小孩子也一路吆喝,孩子们一个个笑脸迎着朝霞,煞是好看。终于把羊群赶到大洼里,羊儿撒欢的吃草,两位老爷爷也偷得半日闲暇,卧在草地上美美地抽上一袋烟,活似神仙般逍遥自在。远方蓝色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云儿这时候也扁的调皮起来,一会儿似羊、似牛似马儿,一会儿又像小孩子,真是美极了。我们小伙伴们就开始在草地里玩“撂骨碌”的游戏,实际上就是一对一摔跤。还有的孩子去捉蚂蚱或者蜻蜓,下河里摸青蛙。不知不觉中,羊儿们就吃饱了,它们就开始相互抵头角力,嬉戏玩耍。 尤其是一些比较强壮的大公羊想挑战领头羊的权威,就会和领头羊单挑,小孩子都喜欢看热闹,这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看看它们谁厉害?其中一只年轻力壮的大青羊非常高大,一身腱子肉外加一双大羊角非常拉风,它经常和领头羊决斗。只见它高高跃起,一头撞向领头羊,当然那只领头羊也好不客气,猛力一蹬,用双角迎击大青羊,只听“嘭”的一声,两只羊撞在了一起,大家都开始用力死死抵住对方,谁也不肯后退半步。我们这时候就分成两派,在旁边不断地为它们叫好加油,两只羊儿也好像是受到了鼓舞,干的更起劲了,大概一袋烟的功夫,那只大青羊终于坚持不住了,被领头羊顶了一个底朝天,落荒而逃了。我们就都鼓起了掌,领头羊虽然累的气喘吁吁,但是头高高昂起,向着天空“MIAN”的一声,响彻天空,就像一个得胜的将军在巡视自己的领地,想当霸气!
中午到了,我们开始返航,吃饱肚子的羊儿们不紧不慢,也不再调皮到处跑了,可是我们的肚子开始哇哇叫了,我们就加紧往家里赶。等回家后把羊儿关到羊圈里,我就在父母的催促下洗手吃饭,然后美美地睡个午觉去了。
03印娃娃模
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成长于八十年代,那时候的农村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地方,但是人们的脸上却经常挂着笑容,感觉生活有滋有味,有奔头。对于我们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是没有玩具可买的,即使有卖的也买不起,我们那时候玩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比如说娃娃模,四角板,手枪,弓箭等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动手制作娃娃模,每年的初夏来临之前,我和小伙伴下午放学后就从教室里直奔家里的小水沟,那时沟是干枯的,我们就沿着沟底寻找制作娃娃模的材料-一种粘性很大的黄胶土,我们又称它为“胶泥”。这种土质又有韧劲还有可塑性,最适合制作娃娃模。由于这种土质都是埋在松软的灰土下面,我们要挖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一旦找到大家都欢呼起来,每人挖一大块,放在书包里运到沟沿上,然后大家一起带着这些胶泥来到村口的大石头上,当时村口有几个雕字画龙的石碑,据说是清末有钱人家立的,解放后就被村民推倒了,放在村口路边的树荫下,人们在那里可以小坐纳凉。后来就成了我们小孩子制作娃娃模的专用地方了。那几个石碑表面光滑,又大又平整,我们把胶泥放在上面,我们从家里提一桶水,就可以制作娃娃模了。
制作娃娃模的工序比较简单,首先我们把泥土和水混合,然后把胶泥揉在一块,使劲的揉搓,就像家里和面一样,时不时的还要拿起泥块在石碑上摔几下,以增加它的柔韧性。直到我们把黄胶泥揉的圆圆的,光滑滑的,那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就开始拿出借来的模子制作了,这些模子是从高年级的同学那里借来的,估计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买的,只能借给我们一个晚上,明天上学时就得还回去,我猜是主人怕我们给它弄坏了,都比较珍贵吧,据说那些模子都是用土窑烧了三天三夜才出窑的,自然是十分昂贵,据说需要1元钱才能买到一个,根据货币换算,七十年代末的一元钱相当于现在的100元也不止吧,我们这些普通家里的孩子自然是买不起的。那时模子做的都很精美,有好多不同的系列,比如西游记系列,有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白骨精、海龙王等;还有水浒传系列,有武松、李逵、鲁智深、林冲等好汉形象。我们首先拿出一块小泥巴,把它摊平涂到模子里,然后使劲压实,让胶泥和模子完全贴合在一起,接着再压边,用树枝去掉周围多于的泥巴,放在那里过2分钟后,用手轻轻的把泥巴从模子里扣下来,动作一定要慢,千万不要把泥巴扣烂了,那样就前功尽弃了。等我们把胶泥扣下来以后,就可以看到一个模子的图案一样的娃娃模了。这时候都会很兴奋,高声吆喝起来,当然也有不成功的时候,比如胶泥揉的不到火候或者掺水太多,都有可能制作不成功,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推倒重做,不一会儿功夫,石碑上就摆满了我们制作的娃娃模。娃娃模接下来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等娃娃模晾干后,我们按照人头和个人喜好把娃娃模分了,然后各自带回家,放在各家屋顶上或者砖墙上,继续晒干,以后就可以拿着到处炫耀和玩耍了,但是这样处理的娃娃模容易干裂变脆,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碎了。还有一种方式是大家接着再加工,把娃娃模放在火炉上烤,火炉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首先找来几块砖,垒出一个灶来,再在上面搭一个又薄又平的石板,把刚刚制作好的娃娃模放在上面依次摆好,接着就找来木柴和干树枝点火,烤制娃娃模。大概用火烤两个小时候后,娃娃模就初步烧制成功了,这时候娃娃模大多变成金黄色,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非常漂亮。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不成功的,烧制出来的娃娃模一块青色一块黑色的,但是,我们也不舍得扔掉,因为那时候的玩具太匮乏了,又是自己亲手做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再丑也舍不得扔啊。
不知不觉中天就黑了,家里大人开始喊吃晚饭了,我们就把娃娃模分了各自放在书包里带回家去,那时候这些玩具大多是不敢让家里的大人看的,怕大人说我们在外面疯玩,不早点回家干活,我们都是偷偷的放在书包里带回家,等吃过晚饭就开始做作业了,那时候老师布置的作业非常少,不超过5个题目,二十分钟就能完成了,因为那时候上学除了课本基本上没有任何辅导书,老师手里也不过是比我们多了一本参考书而已,也不可能出多少题给我们,不想现在的小学生,课桌上堆的书比人都高,家里的书橱里也全是满满的辅导书,每天放学回家没有两个小时是处理不完作业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那时候的孩子是很幸福的,虽然物资很匮乏,但是童年很快乐,每个孩子的眼里都有光。再看看现在的孩子吧,他们虽然吃的好、玩的高级、玩具也很丰富,但是他们大多数活的很累、很卷,这样长大的孩子能幸福吗?
等到晚上睡觉时,大人劳累了一天很快就睡着了,这时候我躺在被窝里,把白天做好的娃娃模偷偷的拿出来,端详把玩很久,简直是爱不释手,最后实在困的不行了,才抱着娃娃模懵懂地睡去,我想晚上即使做梦也会笑醒吧。
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一个片段,已经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家里的房子里找寻那些娃娃模,随着几次搬迁、几次翻盖新房,估计是很难找到了,但关于娃娃模的记忆将永远伴随我的一生!
04摔泥巴
我在孩提时代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摔泥巴,夏季的中午,我每次放学回来以后,草草地扒拉几口饭,喝上一勺子凉水,就急着跑出去找小伙伴玩摔泥巴的游戏,泥巴是从水坑边上一块取回来的,然后大家每人等分一大块泥巴,大家找一个平坦的石头,像大人揉面一样用力在上面把泥巴揉揣,等泥巴变得柔韧不易散开时,我就把它做成一个大碗的形状,放在手上高高举起,碗口向下,用力摔在地面上,只听“嘭”的一声,泥巴碗的底面就出现一个类圆形的洞洞,琐碎的泥巴四处飞溅。另一个小伙伴就把自己的泥巴团成一个圆球,大小和洞的体积差不多,放在洞上就算把碗底补上了,这个用泥巴团成的圆球就是我的战利品,我把圆球和破碎的泥巴碗一块收起来,把它们捏合在一起,下次就可以做一个更大的碗。这时就该轮到我的小伙伴摔他的泥巴碗了,他摔出的洞我也必须拿自己的泥巴给他补上。然后就是下一轮比赛,看看谁摔出的洞洞大,谁就赢的泥巴多,这样几轮比赛下来,有的人手头的泥巴就会越来越少,而另一个手里的泥巴就会越来越多,最后当一方的泥巴补不上另一方摔出来的洞时,就算输了,输的一方就很泄气,赢的一方自然神气多了,就像打仗获胜的将军一样,这次游戏也就停止了。然后大家再重新等分泥巴一较高低。这个游戏虽然简单,但是大家却玩的不亦乐乎,脸上、手上和身上到处弄的都是泥巴,大家都不以为然,只是陶醉在儿时的争抢好胜里面,现在想想那时的孩子心里面真的很纯净,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一块小泥巴就能伴随我们快乐地长大,这也算是上天对我们农村孩子的馈赠吧!现在我和女儿谈起我摔泥巴的情形,她始终张大嘴巴,摆出一副不可置信的摸样,我知道她是怎么也不会理解我贫苦的童年里把一块脏兮兮的泥巴当做玩具而爱不释手的。她的世界里玩具都是从商场里或者网上购买的,玩的泥巴那也是用五颜六色的橡皮泥替代的,既干净又漂亮,价格
自然不低,而我那个时代花一角钱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大人是绝对不允许孩子把钱花在玩耍上面,那对我来说是多么奢侈的行为啊!
然而我现在还时时记起和小伙伴玩泥巴的场景,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时间是最不经用的,转眼已过半生。儿时的记忆渐渐模糊,但是甩泥巴的印记却越来越明晰,似乎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05做弹弓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打鸟玩,各种鸟类包括麻雀、咕咕鸟、大吗嘎子等,小燕子是不打的,据说是益虫。打鸟就必须先做弹弓,做弹弓的材料主要是弹弓架、橡皮筋和牛皮。弹弓架一般选用柳树的Y字形树枝,把外皮去掉,里面是雪白的木质材料,当然也可以选楝子树枝,那个更有柔韧性,只是不好遇到罢了。橡皮筋是越粗的越有劲,射程也越远,但是比较费力拉开。牛皮则是取来做包裹石子的拉手。弹弓的子弹主要是实用圆圆的石子或者是土坷垃,硬度要足够才能把鸟打下来。
制作弹弓的工序基本是这样的:首先是选取一个左右粗细基本对称的Y字形树枝,去掉尾部和左右的头部,做出一个近似Y字形来。然后在左右头部开个槽子,分别系好两根橡皮筋,两根橡皮筋的另外两端系在牛皮上,一个简单的弹弓就做好了。
我们一般喜欢在冬天的下午放学后去打鸟,因为冬天树叶都落了,小鸟藏在树上一眼就能看到,我们看到枝头的麻雀后就悄悄地溜到树下,左手举起弹弓,瞄准麻雀,右手使劲拉开皮筋,等确认准头以后松开手,石子“嗖”的一下就射出去了,如果运气好的话就打中了,小麻雀应声从树上掉下来,我们一拥而上把它抓住,放进准备好的口袋里。一般情况下是打不准的,忙活一下午也就能够打下来四五只。当然如果运气特别好也可以打到大吗嘎子,它是一种特别大的鸟,全身乌黑乌黑的。等到太阳落山,我们就找一个田间地头,挖一个简单的锅灶,找来干树枝点火烤小鸟吃,直到烤的呲呲冒油,我就开始品尝美味了,那种原始肉香的味道非常鲜美,尤其是在那个物质及其匮乏的时代。到现在还时时记起这种味道,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现在虽然也能出去吃到各种各样的烧烤,食材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再也不是小时候的那个感觉了,我想这不仅仅是没有以前的味道了,可能也是再也找不到儿时的玩伴在一起嬉闹开心的日子了。
很赞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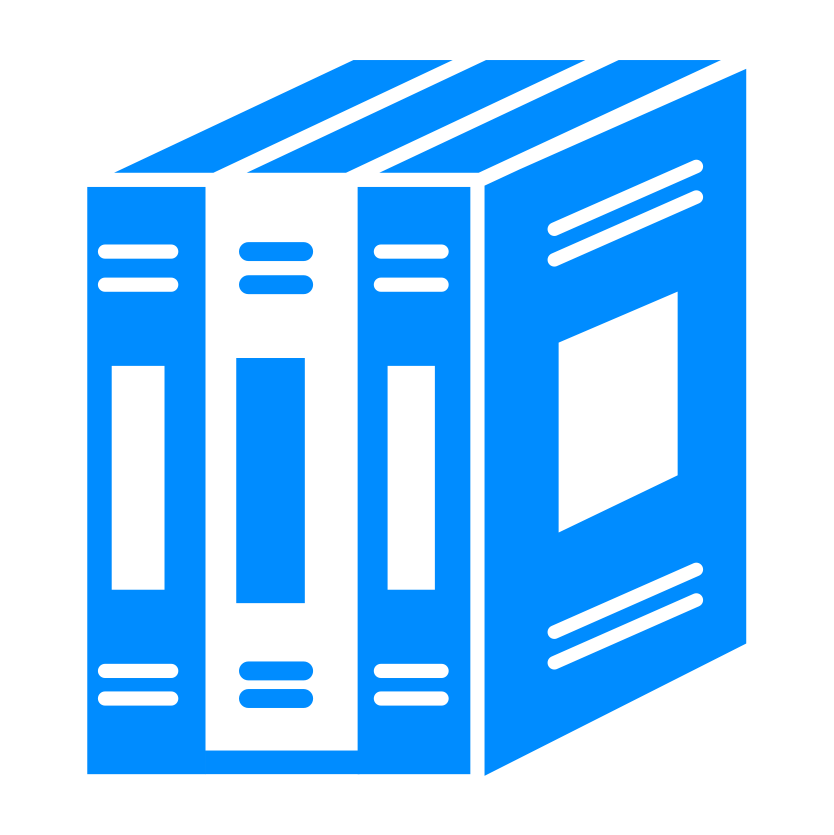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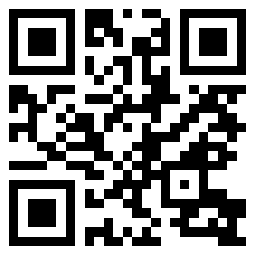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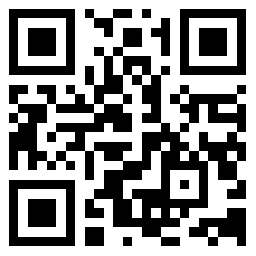
 微信收款码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